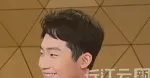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樊振東德國歸來為何更強?

2/3
2025年4月18日,貝內迪克特·杜達在比賽中回球。 新華社發
作為奧運冠軍的他,估計這樣的局面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但我認為他因禍得福,因此開啟了一段漲球之旅。理解這一點,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:
第一,歐洲選手的另類特性。我作為桌球業餘球友,在德國期間和眾多德國球友交過手,我發現德國球友和我們中國球友有一個很大的差異點,德國球友中有獨特打法的人比較多,這又和他們愛鑽研的特質密不可分。我自己就遇到好幾位這樣的球友,比如,有位用沒有膠皮的光板打球,要知道沒有膠皮就沒有旋轉,懂點桌球歷史的人都知道,膠皮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桌球的打法。我看他拿個光板以為是菜鳥,一交手就發現我完全不是他對手,周邊的人也都打不過他。
實際上,羅曼·魯伊斯就是這樣一位另類球手的典型代表。一般選手都是用手接球童拋過來的球,他不是,他一共有三種接法:第一種用球拍接,把球吸在球拍上,這個技術來自羽毛球。第二種用腳接,不用說這個技術來自足球。第三種最奇葩,用嘴接,含在嘴裡。這應該違規了,因為會使桌球變濕、變形,會影響比賽。
他之所以贏了樊振東,一個原因是他相當有迷惑性的發球。他發球引拍動作非常大,看上去像個業餘選手,但這是他獨創的一個段線發球方式。尤其是他有一個「草莓擰」,也是他獨創的,看上去像擰實際上是挑和彈擊,第一次和他打球極不適應。
羅曼·魯伊斯綜合排名不高,所以他沒有機會參加國際大賽。如果樊振東不是到德國來打俱樂部,這輩子他也碰不到魯伊斯。
漲球之旅
第二,相對應地,中國桌球長期採用封閉式、系統化、標準化的國家隊模式,訓練密度大、技術細化程度極高,所有隊員都在統一體系內磨鍊「旋轉強、節奏快、銜接密」的先進打法。在這樣的環境中,對抗質量非常高,但也存在一定的「同質化」:隊內技術結構相似,彼此極為熟悉,很難再給樊振東製造真正陌生的刺激。
相比之下,德國和整個歐洲的桌球生態完全不同。它是開放的、分散的、自由化的,以俱樂部體系為核心,各種風格的選手並存,強調個性化打法、技術創新和落點多變。許多歐洲球員擁有「非中國體系化」的怪球技術,除了魯伊斯的「草莓擰」、斯奇里伯的極端側擰、瑞典和法國選手的長台大弧圈等,這些技術在中國隊內部幾乎沒有人能完整模擬。
樊振東初到德國,連續輸球,說明他第一次真正遭遇了體系外的「陌生旋轉與奇異節奏」,這些混亂、難判且非典型的球路強迫他重新校準判斷系統,提升接發球質量,強化對變化旋轉的敏感度,並重建節奏控制能力。換句話說,德國環境強行打破了他在國家隊中形成的「穩定舒適區」。
11月18日,上海隊選手樊振東在比賽中慶祝。當日,在澳門舉行的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桌球男子團體四分之一決賽中,他以3比2戰勝河北隊梁靖崑。新華社記者 梁旭 攝
第三,樊振東是頂級「吸收型」選手。
也許有人會問,去國外打球的中國人很多,為什麼只有樊振東漲球這麼明顯?這就涉及樊振東自身原因了。
首先,他的技術底盤極其紮實,力量儲備、擊球質量、本體穩定性本就處於世界頂尖,而在德國面對大量高質量的外協會左手、怪膠、異質打法,他原本少接觸的技術空白被迅速暴露,從而給他提供了明確、集中、可量化的提升方向。
其次,樊振東的學習效率極高。他屬於「高速吸收型」選手,只要看到新問題,就能迅速在訓練中建立解決方案,而德國俱樂部自由度大的訓練環境給了他更主動的試錯空間,使他得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針對性調整。
心理層面同樣關鍵。離開國家隊高度結構化體系後,他的壓力反而下降,擺脫「必須贏」的狀態,讓他進入更放鬆、開放、敢於創新的心理區間,有利於打磨球路、節奏變化等長期被忽視的細節。
此外,在德國他需要承擔更多比賽密度和更直接的個人責任,這種「必須自己解決問題」的氛圍,強化了他的臨場判斷、搶節奏能力與危機處理能力。
作為奧運冠軍的他,估計這樣的局面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但我認為他因禍得福,因此開啟了一段漲球之旅。理解這一點,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:
第一,歐洲選手的另類特性。我作為桌球業餘球友,在德國期間和眾多德國球友交過手,我發現德國球友和我們中國球友有一個很大的差異點,德國球友中有獨特打法的人比較多,這又和他們愛鑽研的特質密不可分。我自己就遇到好幾位這樣的球友,比如,有位用沒有膠皮的光板打球,要知道沒有膠皮就沒有旋轉,懂點桌球歷史的人都知道,膠皮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桌球的打法。我看他拿個光板以為是菜鳥,一交手就發現我完全不是他對手,周邊的人也都打不過他。
實際上,羅曼·魯伊斯就是這樣一位另類球手的典型代表。一般選手都是用手接球童拋過來的球,他不是,他一共有三種接法:第一種用球拍接,把球吸在球拍上,這個技術來自羽毛球。第二種用腳接,不用說這個技術來自足球。第三種最奇葩,用嘴接,含在嘴裡。這應該違規了,因為會使桌球變濕、變形,會影響比賽。
他之所以贏了樊振東,一個原因是他相當有迷惑性的發球。他發球引拍動作非常大,看上去像個業餘選手,但這是他獨創的一個段線發球方式。尤其是他有一個「草莓擰」,也是他獨創的,看上去像擰實際上是挑和彈擊,第一次和他打球極不適應。
羅曼·魯伊斯綜合排名不高,所以他沒有機會參加國際大賽。如果樊振東不是到德國來打俱樂部,這輩子他也碰不到魯伊斯。
漲球之旅
第二,相對應地,中國桌球長期採用封閉式、系統化、標準化的國家隊模式,訓練密度大、技術細化程度極高,所有隊員都在統一體系內磨鍊「旋轉強、節奏快、銜接密」的先進打法。在這樣的環境中,對抗質量非常高,但也存在一定的「同質化」:隊內技術結構相似,彼此極為熟悉,很難再給樊振東製造真正陌生的刺激。
相比之下,德國和整個歐洲的桌球生態完全不同。它是開放的、分散的、自由化的,以俱樂部體系為核心,各種風格的選手並存,強調個性化打法、技術創新和落點多變。許多歐洲球員擁有「非中國體系化」的怪球技術,除了魯伊斯的「草莓擰」、斯奇里伯的極端側擰、瑞典和法國選手的長台大弧圈等,這些技術在中國隊內部幾乎沒有人能完整模擬。
樊振東初到德國,連續輸球,說明他第一次真正遭遇了體系外的「陌生旋轉與奇異節奏」,這些混亂、難判且非典型的球路強迫他重新校準判斷系統,提升接發球質量,強化對變化旋轉的敏感度,並重建節奏控制能力。換句話說,德國環境強行打破了他在國家隊中形成的「穩定舒適區」。
11月18日,上海隊選手樊振東在比賽中慶祝。當日,在澳門舉行的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桌球男子團體四分之一決賽中,他以3比2戰勝河北隊梁靖崑。新華社記者 梁旭 攝
第三,樊振東是頂級「吸收型」選手。
也許有人會問,去國外打球的中國人很多,為什麼只有樊振東漲球這麼明顯?這就涉及樊振東自身原因了。
首先,他的技術底盤極其紮實,力量儲備、擊球質量、本體穩定性本就處於世界頂尖,而在德國面對大量高質量的外協會左手、怪膠、異質打法,他原本少接觸的技術空白被迅速暴露,從而給他提供了明確、集中、可量化的提升方向。
其次,樊振東的學習效率極高。他屬於「高速吸收型」選手,只要看到新問題,就能迅速在訓練中建立解決方案,而德國俱樂部自由度大的訓練環境給了他更主動的試錯空間,使他得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針對性調整。
心理層面同樣關鍵。離開國家隊高度結構化體系後,他的壓力反而下降,擺脫「必須贏」的狀態,讓他進入更放鬆、開放、敢於創新的心理區間,有利於打磨球路、節奏變化等長期被忽視的細節。
此外,在德國他需要承擔更多比賽密度和更直接的個人責任,這種「必須自己解決問題」的氛圍,強化了他的臨場判斷、搶節奏能力與危機處理能力。
 福寶寶 • 7K次觀看
福寶寶 • 7K次觀看 董寬楓 • 14K次觀看
董寬楓 • 14K次觀看 董寬楓 • 20K次觀看
董寬楓 • 20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15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15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3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3K次觀看 趙嵐楠 • 7K次觀看
趙嵐楠 • 7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3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3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 趙嵐楠 • 10K次觀看
趙嵐楠 • 10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7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7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9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9K次觀看 趙嵐楠 • 14K次觀看
趙嵐楠 • 14K次觀看 福寶寶 • 6K次觀看
福寶寶 • 6K次觀看 福寶寶 • 7K次觀看
福寶寶 • 7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 福寶寶 • 3K次觀看
福寶寶 • 3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16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16K次觀看 趙嵐楠 • 13K次觀看
趙嵐楠 • 13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5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5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3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3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4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11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11K次觀看 伏嵐晨 • 6K次觀看
伏嵐晨 • 6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