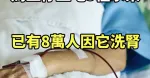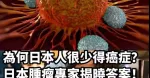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真的只是懶得跑完整後續

3/3
「我那時看父皇站在將士們的屍體前投降,只覺得諷刺。」三哥終是落了淚,額上青筋突起,「這樣的國家,從根上就爛透了。」
我不知如何安慰他,一切已成定局,我總不可能攛掇他現在去刺殺齊硯,一舉奪權。
如三哥所說,殷國從根上就出了問題,饒是他守住了這一次,往後還有無數次。為君者不仁,其國終將覆滅。往好了說,對殷國百姓而言,苦日子興許還快到頭了。
靜默良久,倒是三哥自己想開了,揉揉我的頭道:「吃得有些多,我帶你去消消食吧?」
我覺得不對勁,「去哪兒?」
三哥:「天牢……」
我:「……」
我:「是齊硯的意思吧?」
三哥摸了摸鼻子,訕訕道:「嗯。」
那就很合理了,我利索地站起來,「那走吧。」
三哥卻嘟囔了一聲:「你倒是聽他的話。」
我覺得莫名其妙,「那你不也聽他的話嗎?不然為啥要帶我去天牢?」
三哥:「……」
想來若是梁知意看到這一幕,會罵我和殷臨二人毫無氣節。
但她管得著呢。
天牢關著我父皇,還有一眾我見過或沒見過的兄弟姐妹,而三哥的目標很明確,他是帶我來見父皇的。
昔日的一國之君如今身著囚服,披頭散髮,面容憔悴,見我的第一句便是:「你這個不孝女!」
話音剛落就被旁邊的獄卒踹了一腳,「皇后面前,休得無禮!」
感覺這麼一踹,他的一把老骨頭都碎了。
我不想理會他,問三哥:「齊硯讓我見他,是想幹什麼?」
三哥看著老頭子,目光幽幽,「讓你知道你母妃的過往。」
「陳年舊事,我……朕!朕早就忘了!」
又是一腳。
他吐出一口血,蜷縮在地上。
三哥別開眼,「之前就已約定好,你若不說,什麼下場你自己清楚。」
他仍在含糊地咒罵:「逆子……逆女……」
罵完後,在昏暗的牢房裡,他心不甘情不願地說起往事。
早年間,殷韋還是個皇子的時候,曾喬裝打扮混入齊國,不慎遭受暗算,身負重傷。
我娘就是在那時出現的,山野田間,荒無人煙,我娘心生不忍,便救下了他。相處之中,殷韋對我娘心生愛慕,一番表白後卻聽我娘道明別無他念,一時心生怨懟,竟在傷愈之際迷暈了我娘,強綁去了殷國。
若我娘是個鄉野婦人,那齊國也不會察覺此事,奈何我娘其實全名為齊心姚,是定國公的小女兒,因自幼體弱便養在鄉間不問世事,卻不料因此遭難。
那會兒齊國皇室正亂,定國公忙於安穩各方勢力,又因我娘身邊向來有暗衛保護,便沒有多問。不想殷韋也帶著一隊人馬,用骯髒手段將暗衛盡數斬殺,強取豪奪。
待定國公發覺此事,我娘已改名換姓,困於殷國深宮。
殷韋自暗衛出現後便知我娘身份不凡,但色膽包天,終究下了毒手。
我娘醒後,恨死了他,用過各種手段逃跑,都被抓了回去。
殷韋愛她,又恨她不愛他,威逼利誘,軟硬兼施,均無成果。於是後來,他就冷落了她,哪怕得知她懷孕,生下公主,他都不願再踏入她的宮門半步,甚至得知我娘死訊那一刻,他也只是愣了一瞬,便擁著新寵,笑道:「接著奏樂,接著舞。」
我不曾知道這般詳細的過往,也不知我娘受了這麼多苦難。記憶里的她向來是溫婉的,偶爾眉間會籠上一股愁緒,但目光移向我時那一切就都消散了。
她只會輕輕喚我:「杳杳,過來,娘今天教你別的。」
種菜和養雞的技能便是我娘教我的,除此之外,她還會編螞蚱、捉麻雀等等。我一直以為她就是普通的農婦,不承想她原是定國公的女兒。
再看到對面的糟老頭子,我覺得有點噁心,也真的吐了出來。
「杳杳,沒事吧?」三哥擔憂地拍了拍我的背,嘆氣,「這些事本不打算告訴你的,可……」
可齊硯知道,而且希望我也知道。
我突然明白了齊硯的目的,望向那個罪魁禍首,笑道:「我要去謝謝他,滅了你的國。」
殷韋臉色變了又變,突然大發雷霆,「你這個不孝女,你在說什麼!朕是父皇,你卻不知孝道,同你娘一樣可惡!朕是她夫君,她卻……」
後面都是些瘋言瘋語,我不想再聽,便與三哥一同離開了。
出來後,我看了看正好的太陽,問三哥今後打算,他苦笑著說:「難道這能由我做主嗎?」
哦,是了,殷國滅亡,如今殷家人,都是亡國奴,階下囚,萬般都由不得自己。
可我如今有了私心,至少不希望三哥落得與他們一樣,便道:「三哥若是信得過我,我能幫三哥做主。」
他愣了下,「你要怎麼?」
我十分認真,「色誘一下齊硯就好。」
殷臨:「?」
11
這段話必然傳到了齊硯耳中,他故意派人通知我今晚他不召人侍寢,自己一個人睡。
這麼點破事也值得他昭告天下,我多少有點無語。
小翠知曉我要去「色誘」齊硯後表示大力支持,花了半天工夫打扮我,奇裝異服讓破抹布都嚇了一跳,直接不認識我了。
我:「……」
這丫頭爭寵的心果然沒有消失!
小翠很是滿意,「娘娘貌若天仙,必定討陛下喜歡。」
於是我就被這麼送到了齊硯的寢殿,到達時他還在御書房處理政務,便留我一人在寢殿里等人,一如剛來那日。
可惜人嬌慣了,頂著滿頭珠翠,穿著奇怪的裙衫,我很不適應,想著與齊硯什麼樣都見過了,我就自作主張把小翠的心意全部脫了下來,穿著單衣在床上等齊硯,然後等睡著了。
醒來時齊硯正躺在我身側,用指尖描我的眉,見我睜眼便勾唇,「你就是這樣來『色誘』我的?」
我尚未完全清醒,什麼「色誘」更是早已拋在腦後,現在只會習慣性往他懷裡滾去,想順勢抱住他勁瘦的腰。
手剛觸到布料就被他推了回來,聲音微涼,「朕可說過今晚不召人,皇后怎麼敢明知故犯?」
我眨了眨眼,終於清醒了,討好地看著他,「沒有陛下,臣妾一個人睡不著。」
「是嗎?」他坐了起來,離我更遠了,「朕來的時候皇后已經睡得十分香甜,並不像是徹夜難眠的樣子。」
我:「……」
那不還是你批奏摺批得太晚。
我心裡嘟囔,面上不敢顯現,把姿態放得更低了些,向他拋媚眼,「陛下,墨之……長夜寂寞,真的不可以陪一陪杳杳嗎?」
齊硯瞬間面色難看,「夠了,你不要再說了。」
我順從地恢復正常,「你看,我確實做不到,沒這個能力知道吧?」
色誘,我從出生起就沒做過這種事,第一次做肯定很噁心。
嘻嘻,就是故意噁心齊硯。
齊硯氣笑了,勾起我脫下的放在床邊的一件衣服,對我挑眉,「杳杳,要顯誠意,便穿這件給我看吧。」
那是小翠宣稱的絕密武器,一條半透明的紗裙……
我糾結了會兒,順從地拿過這件裙子,然後當著齊硯的面慢吞吞換衣。
齊硯看我的目光越發幽深,最後一把將我拽過去,「杳杳,若我要下地獄,就拉你一起好不好?」
我:「齊硯,我想活著……」
他笑了,並堵住我的唇,「如今你可選不了。」
我……那你問我幹啥?
一夜荒唐,第二日醒來,我才想起要幫三哥求個官職。
都怪齊硯,害得我忘了。
他下朝時便見我一臉幽怨,瞭然道:「你三哥的事,我會給你安排好的。他本就是個有才之人,心中也有抱負,我不會屈才。」
齊硯給三哥安排的官職便是掌管原先殷國的土地,也算了卻他心中一樁憾事。
重點是,這道旨意前幾日就有了,也就是說,我色不色誘都一樣。
齊硯再次笑得找打,「昨晚那件紗衣很配杳杳,我會命司衣局多仿製幾件,都送到你宮裡去。」
我完全一副「都行,你開心就好」的狀態。
齊硯又問我,想如何處置殷韋及其子女,「想來那些往事你都知道了,所以如今,選擇權在你。」
我卻想起別的,「你一早就知道這些事嗎?」
他點點頭,「我幼年時與你母親見過面,後來她失蹤,我也就打探過消息,具體詳情還是前幾年我的暗衛查出來的。」末了又問我,「恨他嗎?」
沒說是誰,但我與他都知道是誰。
「你讓我見他,讓我知道這些事,是想讓我恨他嗎?」
齊硯微怔,輕輕撫上我後頸,「杳杳,我知道你性子不喜爭鬥,但是該恨的人,就應該恨。還記得那日在天牢的情緒嗎?那就是恨意,比愛濃烈,比愛持久,能支撐你走很遠很遠。」
我拉住齊硯的衣袖,弱弱道:「可我不想恨,恨太累了,而且,我也沒打算走很遠很遠,因為我懶得走……」
就像曾經某日,他和我展示他用美人骨做的扇,道我若是害怕可以現在就逃回殷國。
我回道:「太累了,懶得動……」
活著便很辛苦了,若是還要分出精力去恨誰,實在太過勞累了。
齊硯眼底的陰鬱霎時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盈盈笑意和幾分無奈,「你啊……總有一日是懶死的。」
我點頭,「嗯,也不是不行。」
一旁的小翠都嘆了一聲。
殷韋最終被判了斬立決,齊硯替我拿的主意,說是既然我不敢殺人,就他來替我殺。
我的那些個兄弟姐妹都被發配到了邊疆,只有我三哥要去殷縣上任。
出發那日,他一步三回頭,很是不舍,「若是過得不順遂,定要寫信給我。」
我覺得好笑,「又不是此生都見不到了,哥哥這是做什麼?」
他似乎瞄了一眼齊硯,對我笑道:「你可拉倒,我若不主動來見你,以你的性子,肯定八百年都不會來看我。」
哦,這個確實。
最後是齊硯喚回出神的我:「杳杳,起風了,我們回去吧。」
12
一切塵埃落定後,還剩下一些流言,道是當年梁國敗得可惜,說梁氏姐弟是苦命人。
這都是老生常談,算不得什麼,只是不知從何時起,有人傳當今聖上非齊國皇室血脈,實乃冒名頂替之徒。
齊硯不曾與我說過這些,我都是從小翠和江寧瑤口中得知這些往事。
話說當年齊國與梁國還算是勢均力敵,齊國曾送一名皇子赴梁國,那便是齊硯。有人傳,其實當年的皇子早已遭到梁國毒手,死於非命,如今這個齊硯不過是一個頂替身份的無名小卒。
與此同時,還有人翻出齊硯的舊帳,稱其不是什麼仁君,相反的,其實他殘暴不仁,殺人如麻。梁氏後代近乎被絕,往年治理天下時也用過不少雷霆手段,害過不少無辜亡靈,還有早年送進宮的那些美人的家人也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,一遍遍哭訴自己女兒何等無辜可憐。
一時之間,民心大亂。
聽聞這幾日早朝,已有一些臣子進言,明里暗裡質疑齊硯的血統是否純正,說他們效忠的是齊家人,絕不許有人濫竽充數,魚目混珠。
齊硯卻毫無回應,只是一如既往地明面上寵著梁知意,半夜又翻窗戶來尋我。
我總覺得他瘦了不少,便在他吻我時避開他,輕聲道:「早些睡吧,你該多休息。」
他作亂的手就在我腰間停住,黑夜中他的眸子似乎在發光,「心疼我了?」
我假裝聽不出他話中的笑意,「嗯,怕你猝死了,我就沒有靠山了。」
他掐了把我的腰,「沒良心的。」
我不說話,只蹭了蹭他的胸膛。
半晌,他道:「杳杳,過幾日,隨我一起去秋獵好不好?」
表面是商量,實際是通知,我沒有拒絕的權力。
江寧瑤藉口要照顧咪咪和破抹布,不願一同過來,倒是在我出發前一日提醒我,要注意安全。
防的誰呢?自然是一同前往的梁知意。
自從殷國投降,梁知意便有些看不上我,不再像以往那樣攛掇我與她統一戰線。我倒是樂得她離我遠些,只是秋獵期間,我倆不得不打個照面。
「原先擔心皇后娘娘會傷心過度,還好看著氣色不錯。」
她笑盈盈的,但就是讓我不舒服,我敷衍答道:「本宮日日吃好睡好,自然氣色不錯。」
「是嗎?」她笑了下,又作憂愁狀,「嬪妾聽聞邊疆苦寒,不知娘娘的兄弟姐妹,是不是能吃好睡好。」
我打了個哈欠,「勞淑貴妃掛心,若是這麼擔心本宮的兄弟姐妹,不如哪日去邊疆親自看看。」
她臉色白了白,鄙夷地看了我一眼,不再說話。
我知她看不起我,也不指望她理解我。畢竟聽聞梁氏後代彼此之間關係親厚,她為族人鳴不平是正常的,但我又沒有那樣良善的族人,自然也就做不到她那樣臥薪嘗膽。
道不同,不相為謀。
齊硯瞧出我不願搭理梁知意,便提出帶我一同去狩獵。
可我懶得動,「我不會騎馬。」
他一臉意料之中,「我帶著你騎,又或者,你在這兒和淑貴妃一起等我回來。」
我:「我和你一起去……」
獵場是一片森林,青綠與金黃交錯,偶有落葉飄下,還有馬蹄踏下時的沙沙聲響,倘若忽略齊硯落在我後頸的吻,這一幕不失為難忘的美景。
我側了側身子,無語道:「齊硯,你不是出來打獵的嗎?都已經跑過去兩頭梅花鹿了!」
他笑了一聲,「不急。」隨後就是扯著韁繩,讓馬兒慢悠悠地走在林間,就像是,在等待著什麼。
良久,大約已是走到林深處,不知從何飛來一箭,驚得馬兒狂奔起來。
風在耳邊呼嘯,還有數不清的箭從四面八方破空而出,多數都被附近的暗衛擋下,少數漏過來的,也被齊硯避開。
他一手拉著韁繩,一手攬著我的腰,還笑得出來,「害怕嗎?」
我緊緊靠著他的胸膛,都不知此刻狂跳不止的,是我的心臟還是他的。
我聽到自己問:「我們會死嗎?」
齊硯輕笑,胸腔震動,「杳杳,你不會死的。」
是啊,我不會死的,因為射向我們的箭,最終,還是被齊硯接下了。
待馬兒中箭倒地,齊硯抱著我在地上翻滾數圈停下,我才發現他身上的異樣,後方已無追兵,但前方,也只有深不可測的密林,仿佛蒼茫天地之間,只剩下我與齊硯二人。
齊硯已經昏過去了,他身後的箭似乎早已被他自己折斷,只剩下一小段插著,因為身著玄衣,所以流出多少血都看不太出來。我也是恍然才發覺,草木香氣之中,還有那麼一股濃烈的血腥味。
他說,杳杳,你不會死的。
因為,他都幫我擋下了。
又或者,這些本就是衝著他來的。
「白痴。」
我把他狼狽的臉擦拭乾凈,又費力將他拖到隱蔽一點的地方靠到樹旁。
萬分慶幸,幼時我娘教過我野外的草藥,我憑著模糊的記憶力,在周圍找到了一些止血的藥草,隨後咬著牙將他後背的箭拔出,把嚼碎的草藥敷上,再撕下一段衣料替他包紮。
一番動作下來,我已是滿頭大汗,一半是他沉得慌,我要用很大的力氣搬動他,另一半,是我的心始終揪成一團,包紮時手都在微微顫抖。
最後我累極,靠在齊硯身旁睡了過去。
做了場怪夢,夢的最後齊硯對我露出悲涼的笑,再不言語。
醒來時已是傍晚,齊硯仍在昏迷。
太陽落山,林間有股陰濕的寒氣。我摸了摸齊硯的額頭,有薄薄的一層汗,冰涼涼的,頓時心下一沉,別無他法,只好面對面緊緊抱著他,再用他的外衣將我們兩人一同裹住,企圖渡些熱氣過去。
四周越來越暗,偶有鳥兒歸巢的厲聲,還有動物從灌木叢中穿梭而過的沙沙聲。
我又有些困意,但不敢睡,就一直在齊硯耳邊碎碎念,說的都是沒頭沒尾的東西。
「破抹布越來越大了,性格也變調皮了,他們都說破抹布長得不好看,可我覺得長得挺好看的,怎麼說,有種怪異的美。
「你和我說喜歡吃雞蛋羹是不是騙我的啊?我還給江寧瑤做過雞蛋羹,她說是最普通不過的雞蛋羹了。
「要我說,就怪你下午放跑了那兩隻梅花鹿,不然現在我們也不至於餓著肚子,現在烏漆嘛黑的,我晚上眼神也不好,從哪兒給你弄吃的呢?
「要是我們在農村就好了,我好歹還能給你偷點菜和雞蛋,這個林子又大又不好走,到時候餓死你也別怪我。
「你什麼時候能醒過來啊?以前都是你把我吵醒的,現在該換我吵醒你了,給個面子嘛……」
我囉里吧嗦說了一堆,最後聽見齊硯沙啞的聲音:「我都不知道,你原來話這麼多,吵得我頭疼。」
我歡喜地貼了貼他的額頭,確認他沒有發燒後嫌棄道:「你是背部中箭,要痛也應該是背痛。」
他悶悶地笑了,「怎麼不跑?」
我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他,「腦子也中箭了?」
他只笑,「我知當初你是被迫跟著我,如今我或許不再是皇帝,也就強迫不了你,若你想走,現在是最好的時機……嘶,你幹什麼?」
我咬了一口他的嘴,無語道:「想看看你的嘴巴到底有多硬。」
「殷嬈……」
我站了起來,打斷他,「說這麼多沒用的,還不如好好看看周圍,想想我們怎麼出去。」
他夜間視力也極佳,是唯一可指望得上的了。
齊硯沒動,仍看著我。
我很討厭他這副樣子,好像巴不得現在就被我拋棄,「你以為你很厲害嗎?想讓我幹嗎就幹嗎?我殷嬈真的不想做的事,誰都強迫不了我,你明不明白?而且就算我要走,那也要先回宮拿了東西,帶著破抹布一起走,你以為現在丟下你一走了之,我就能活得很好了嗎?齊硯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啊……」
什麼事都不與我說,擅自主張安排好一切,然後假惺惺說現在願意放我走,我雖然草包,但不至於這麼任人擺布。
「我不管你在下什麼大棋,與什麼人在做博弈,我出來前已經和江寧瑤還有小翠約好了,帶兩隻小兔子給她們玩,你是不是覺得你欠我很多啊?那你就按我的心意還我,先把我帶出這片狗屎林子,然後給我抓兩隻兔子,最後帶我回去!」
我說了好長一段話,仍覺得不解氣,話鋒一轉,「還是說你愛上了梁知意,所以想找個藉口放我走?齊硯你這個負心漢……」
情緒剛到位,齊硯就站起來抱住了我,順勢堵住了我喋喋不休的嘴。
林間,只剩下悉窣聲,和糾纏在一起的呼吸聲。
良久,他嘆道:「我真是怕了你了,一張小嘴這麼會說。」
我仍在氣頭上,撇開頭不想理他,又被他掰了過去。
「抱歉,我不趕你走了,」他溫聲道,「所以你也不許再說離開我的話。」
我:「我從來沒說過,是你自己瞎想出來的吧。」
他靜默了會兒,「好像是的。」
我:「……」
所以這人腦子裡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麼?
齊硯厚著臉皮貼上來,用鼻尖蹭我的臉,「那你也從沒說過不離開我。」
「我又不傻,你總是往梁知意宮裡跑,我幹嘛要說這種倒貼的話。」
他吃吃笑了,「醋了?」
我不想回答,轉移話題道:「你肩傷不疼了?」
他像是才想起來似的,浮誇地倒吸一口氣,「疼。」
我狐疑,「真有那麼疼?」
他點點頭,「嗯。」
我:「嘻嘻,你活該。」
13
打鬧結束,齊硯憑藉優秀的眼力和記憶力,帶著我走出了林子,並正巧遇上了尋我們的人。
也是在燈火下我才發現他臉色白得嚇人,看起來很虛弱,只怕之前的淡定都是裝的。
我霎時紅了眼,急得差點將隨行的太醫扛過來,齊硯卻安撫地拍了拍我的手,「沒事,我答應過你,會好好活著。」
那是好久以前的話了,我都差不多忘了。至此我揉了揉眼,只道:「那你不許反悔,你還要給我抓兔子呢。」
他慘白的唇勾出一抹笑,對旁人道:「讓皇后出去好好休息。」
我自己也確實憔悴不堪,聞言沒有抗拒,乖乖出去,吃飯洗漱,再好好地補了個覺。
醒來已是第二日,侍衛說太醫已經查看過了,除了肩傷,其餘並無大礙,眼下齊硯正在休息。
我不欲打擾他,便站在帷帳門前,問侍衛:「可查出是誰下的手嗎?」
齊硯曾告訴我,那日在天牢里的感覺叫恨,如今我算是再次體會到了。
大概齊硯下過旨,侍衛也沒瞞我,「是淑貴妃的人。」
梁氏姐弟,一個在獵場刺殺齊硯,一個在城內調兵遣將準備篡位。但齊硯大概將一切都算準了,刺殺沒有成功,篡位也沒有成功。昨晚齊硯出事的下一刻,二人就被抓了。
我都不免懷疑,齊硯肩上的傷是不是也是他計劃中的一環。
如此想著,我在給齊硯喂藥時,也就這麼問了。
他似乎也不意外,坦然點頭,「是,苦肉計。」
我:「……」
我理解不了,「為什麼?」
「想知道你愛不愛我。」他的手又緩緩攀上我的後頸,據我的經驗推斷,這表明他的一種掌控欲。
我只覺得白痴,「我若不愛你,會和你睡覺?」
齊硯想了想,「以你的性格,你覺得呢?」
我:「……」
可惡,被拿捏了。
齊硯繼續不緊不慢道:「還記得我以前教你的嗎?那叫恨意,你說太辛苦。所以現在我教你別的,杳杳,你昨晚對我的那番表露,叫愛意。」
我看到了他眼底的執拗與瘋狂,突然明白了些什麼,「若我昨晚決定拋下你獨自離開,我是不是會死?」
齊硯默認了,「還記得我給你看的用美人骨做的扇子嗎?雖然從來沒在你面前殺過人,但我其實不是個好人,在你不知道的角落,我殺了無數人。所以我想,也可以殺了我的心上人。我的真面目就是這樣,殷嬈。」
我思索半晌,感嘆道:「那你挺變態的。」
齊硯:「……」
齊硯扯了扯嘴角,「除此之外,你沒有別的想法嗎?」
我點點頭,「你快點好起來,還欠我兩隻兔子呢。」
齊硯不說話了,只盯著我看,看得我渾身發毛,最後硬著頭皮上前吻了吻他的嘴角,皺巴了臉,「好苦。」
他倏地笑了,按著我的後腦勺深入,末了才笑道:「這樣才能嘗出來,良藥苦口。」
我瞪了他一眼,「流氓。」
待齊硯傷恢復了大半,我們一行人回了皇宮,順帶還有兩隻兔子。
最後江寧瑤與我大眼瞪大眼,提議道:「今晚吃紅燒兔頭吧?」
我覺得甚妙。
此前的事都已被查了個水落石出。此次刺殺,以及之前宮宴上樑知意擋的那一刀,都是梁志敏的人做的。這期間梁志敏還有私底下招兵買馬、圖謀不軌、結黨營私等罪行。梁知意使用迷情香的事也被曝了出來,以及與前朝私通、擾亂朝政等。總之這對姐弟,一夜之間,聲名狼藉,雙雙入獄。
行刑前一夜,梁知意求見我,我犯懶,齊硯卻要帶著我一起過去。
梁知意仍舊挺直脊樑,面上不再一副溫婉神情。
「你怎麼敢一起來的?」她對著齊硯恨恨道。
齊硯擁著我,懶懶道:「你不就是想與她說我的事嗎?那我這個當事人,為何不能在場?」
我不喜歡這種打謎語的對話,「有事說事,沒事我走了。」
還和江寧瑤約好了今晚吃紅燒豬蹄呢。
梁知意一臉「你真可悲」的表情,「你知不知道你身邊是個什麼樣的男人?」
我即答:「一個變態。」
然後齊硯掐了一把我的腰。
我順勢推開他,「你出去,我和她說悄悄話。」
齊硯:「……」
梁知意:「……」
我坐在梁知意對面,撐著頭道:「好了, 你想和我說什麼?」
想說什麼呢?不過是一些陳年舊事罷了。
齊硯確實不是當年那個皇子,他是隨著皇子一同前來的小太監。至於梁知意為何這麼確定,是因為那個皇子就是梁國人殺的。誰都沒想到後來那個小太監冒名頂替,成了齊硯。
我抹了把臉,不太相信,「你確定是小太監?不是什么小侍衛之類的?」
「當然……你什麼意思?」
我摸了摸下巴,「額……據我所知,齊硯不是太監。」
梁知意瞬間瞳孔地震,過了會兒苦笑,「難怪, 我還以為那香對他沒作用是因為他是太監……原來如此,原來如此……」頓了頓, 又問我, 「他殺了你父親,你怎麼還做得到和他待在一起?」
我不想解釋太多,「每個人的境遇不同, 你不應該用你的想法綁架我。若你想告訴我的就是齊硯的身份,那我覺得到這裡就差不多了。」
正欲起身離開, 梁知意又叫住我:「你不覺得這樣一個人很可怕嗎?作為你的枕邊人, 心機如此之重。」
我贊同地點點頭,「是挺可怕的。」
「那你為什麼不離開他?」
我應得理所當然, 「懶得跑……」
那晚齊硯難得只抱著我睡,其他什麼也沒幹。他與我說其實他也是齊國皇子, 但是一個宮女所生,極不得寵。當年只有那個皇子對他好, 所以他喬裝打扮隨他一起去了梁國。不承想遭此不幸,為了報仇,他不得不冒名頂替, 而後大力發展齊國,一舉吞併了梁國。
我不得不感嘆:「好勵志的故事。」
齊硯:「……」
齊硯蹭了蹭我的頸間,「你沒有別的想說的?」
「哦,是有。」我這才想起什麼,「江寧瑤要我求求你, 放她出宮去。」
原來齊硯留她下來,只是為了陪我解解悶,如今他已經處理好了梁國的事, 江寧瑤也覺得宮裡太無聊了,就想出去了。
「這是小事, 」齊硯吻了吻我的脖子, 「你還有別的要說嗎?」
我想了想,「該睡覺了?」
齊硯氣得咬了我一口。
我笑了,「好啦,提問, 為什麼殷嬈不離開齊硯這個變態呢?」
在那一瞬間齊硯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。
我回抱住他,在他耳邊小聲道:「因為她學會了愛意。」
恨意太累人了,還是愛你比較容易。
我不知如何安慰他,一切已成定局,我總不可能攛掇他現在去刺殺齊硯,一舉奪權。
如三哥所說,殷國從根上就出了問題,饒是他守住了這一次,往後還有無數次。為君者不仁,其國終將覆滅。往好了說,對殷國百姓而言,苦日子興許還快到頭了。
靜默良久,倒是三哥自己想開了,揉揉我的頭道:「吃得有些多,我帶你去消消食吧?」
我覺得不對勁,「去哪兒?」
三哥:「天牢……」
我:「……」
我:「是齊硯的意思吧?」
三哥摸了摸鼻子,訕訕道:「嗯。」
那就很合理了,我利索地站起來,「那走吧。」
三哥卻嘟囔了一聲:「你倒是聽他的話。」
我覺得莫名其妙,「那你不也聽他的話嗎?不然為啥要帶我去天牢?」
三哥:「……」
想來若是梁知意看到這一幕,會罵我和殷臨二人毫無氣節。
但她管得著呢。
天牢關著我父皇,還有一眾我見過或沒見過的兄弟姐妹,而三哥的目標很明確,他是帶我來見父皇的。
昔日的一國之君如今身著囚服,披頭散髮,面容憔悴,見我的第一句便是:「你這個不孝女!」
話音剛落就被旁邊的獄卒踹了一腳,「皇后面前,休得無禮!」
感覺這麼一踹,他的一把老骨頭都碎了。
我不想理會他,問三哥:「齊硯讓我見他,是想幹什麼?」
三哥看著老頭子,目光幽幽,「讓你知道你母妃的過往。」
「陳年舊事,我……朕!朕早就忘了!」
又是一腳。
他吐出一口血,蜷縮在地上。
三哥別開眼,「之前就已約定好,你若不說,什麼下場你自己清楚。」
他仍在含糊地咒罵:「逆子……逆女……」
罵完後,在昏暗的牢房裡,他心不甘情不願地說起往事。
早年間,殷韋還是個皇子的時候,曾喬裝打扮混入齊國,不慎遭受暗算,身負重傷。
我娘就是在那時出現的,山野田間,荒無人煙,我娘心生不忍,便救下了他。相處之中,殷韋對我娘心生愛慕,一番表白後卻聽我娘道明別無他念,一時心生怨懟,竟在傷愈之際迷暈了我娘,強綁去了殷國。
若我娘是個鄉野婦人,那齊國也不會察覺此事,奈何我娘其實全名為齊心姚,是定國公的小女兒,因自幼體弱便養在鄉間不問世事,卻不料因此遭難。
那會兒齊國皇室正亂,定國公忙於安穩各方勢力,又因我娘身邊向來有暗衛保護,便沒有多問。不想殷韋也帶著一隊人馬,用骯髒手段將暗衛盡數斬殺,強取豪奪。
待定國公發覺此事,我娘已改名換姓,困於殷國深宮。
殷韋自暗衛出現後便知我娘身份不凡,但色膽包天,終究下了毒手。
我娘醒後,恨死了他,用過各種手段逃跑,都被抓了回去。
殷韋愛她,又恨她不愛他,威逼利誘,軟硬兼施,均無成果。於是後來,他就冷落了她,哪怕得知她懷孕,生下公主,他都不願再踏入她的宮門半步,甚至得知我娘死訊那一刻,他也只是愣了一瞬,便擁著新寵,笑道:「接著奏樂,接著舞。」
我不曾知道這般詳細的過往,也不知我娘受了這麼多苦難。記憶里的她向來是溫婉的,偶爾眉間會籠上一股愁緒,但目光移向我時那一切就都消散了。
她只會輕輕喚我:「杳杳,過來,娘今天教你別的。」
種菜和養雞的技能便是我娘教我的,除此之外,她還會編螞蚱、捉麻雀等等。我一直以為她就是普通的農婦,不承想她原是定國公的女兒。
再看到對面的糟老頭子,我覺得有點噁心,也真的吐了出來。
「杳杳,沒事吧?」三哥擔憂地拍了拍我的背,嘆氣,「這些事本不打算告訴你的,可……」
可齊硯知道,而且希望我也知道。
我突然明白了齊硯的目的,望向那個罪魁禍首,笑道:「我要去謝謝他,滅了你的國。」
殷韋臉色變了又變,突然大發雷霆,「你這個不孝女,你在說什麼!朕是父皇,你卻不知孝道,同你娘一樣可惡!朕是她夫君,她卻……」
後面都是些瘋言瘋語,我不想再聽,便與三哥一同離開了。
出來後,我看了看正好的太陽,問三哥今後打算,他苦笑著說:「難道這能由我做主嗎?」
哦,是了,殷國滅亡,如今殷家人,都是亡國奴,階下囚,萬般都由不得自己。
可我如今有了私心,至少不希望三哥落得與他們一樣,便道:「三哥若是信得過我,我能幫三哥做主。」
他愣了下,「你要怎麼?」
我十分認真,「色誘一下齊硯就好。」
殷臨:「?」
11
這段話必然傳到了齊硯耳中,他故意派人通知我今晚他不召人侍寢,自己一個人睡。
這麼點破事也值得他昭告天下,我多少有點無語。
小翠知曉我要去「色誘」齊硯後表示大力支持,花了半天工夫打扮我,奇裝異服讓破抹布都嚇了一跳,直接不認識我了。
我:「……」
這丫頭爭寵的心果然沒有消失!
小翠很是滿意,「娘娘貌若天仙,必定討陛下喜歡。」
於是我就被這麼送到了齊硯的寢殿,到達時他還在御書房處理政務,便留我一人在寢殿里等人,一如剛來那日。
可惜人嬌慣了,頂著滿頭珠翠,穿著奇怪的裙衫,我很不適應,想著與齊硯什麼樣都見過了,我就自作主張把小翠的心意全部脫了下來,穿著單衣在床上等齊硯,然後等睡著了。
醒來時齊硯正躺在我身側,用指尖描我的眉,見我睜眼便勾唇,「你就是這樣來『色誘』我的?」
我尚未完全清醒,什麼「色誘」更是早已拋在腦後,現在只會習慣性往他懷裡滾去,想順勢抱住他勁瘦的腰。
手剛觸到布料就被他推了回來,聲音微涼,「朕可說過今晚不召人,皇后怎麼敢明知故犯?」
我眨了眨眼,終於清醒了,討好地看著他,「沒有陛下,臣妾一個人睡不著。」
「是嗎?」他坐了起來,離我更遠了,「朕來的時候皇后已經睡得十分香甜,並不像是徹夜難眠的樣子。」
我:「……」
那不還是你批奏摺批得太晚。
我心裡嘟囔,面上不敢顯現,把姿態放得更低了些,向他拋媚眼,「陛下,墨之……長夜寂寞,真的不可以陪一陪杳杳嗎?」
齊硯瞬間面色難看,「夠了,你不要再說了。」
我順從地恢復正常,「你看,我確實做不到,沒這個能力知道吧?」
色誘,我從出生起就沒做過這種事,第一次做肯定很噁心。
嘻嘻,就是故意噁心齊硯。
齊硯氣笑了,勾起我脫下的放在床邊的一件衣服,對我挑眉,「杳杳,要顯誠意,便穿這件給我看吧。」
那是小翠宣稱的絕密武器,一條半透明的紗裙……
我糾結了會兒,順從地拿過這件裙子,然後當著齊硯的面慢吞吞換衣。
齊硯看我的目光越發幽深,最後一把將我拽過去,「杳杳,若我要下地獄,就拉你一起好不好?」
我:「齊硯,我想活著……」
他笑了,並堵住我的唇,「如今你可選不了。」
我……那你問我幹啥?
一夜荒唐,第二日醒來,我才想起要幫三哥求個官職。
都怪齊硯,害得我忘了。
他下朝時便見我一臉幽怨,瞭然道:「你三哥的事,我會給你安排好的。他本就是個有才之人,心中也有抱負,我不會屈才。」
齊硯給三哥安排的官職便是掌管原先殷國的土地,也算了卻他心中一樁憾事。
重點是,這道旨意前幾日就有了,也就是說,我色不色誘都一樣。
齊硯再次笑得找打,「昨晚那件紗衣很配杳杳,我會命司衣局多仿製幾件,都送到你宮裡去。」
我完全一副「都行,你開心就好」的狀態。
齊硯又問我,想如何處置殷韋及其子女,「想來那些往事你都知道了,所以如今,選擇權在你。」
我卻想起別的,「你一早就知道這些事嗎?」
他點點頭,「我幼年時與你母親見過面,後來她失蹤,我也就打探過消息,具體詳情還是前幾年我的暗衛查出來的。」末了又問我,「恨他嗎?」
沒說是誰,但我與他都知道是誰。
「你讓我見他,讓我知道這些事,是想讓我恨他嗎?」
齊硯微怔,輕輕撫上我後頸,「杳杳,我知道你性子不喜爭鬥,但是該恨的人,就應該恨。還記得那日在天牢的情緒嗎?那就是恨意,比愛濃烈,比愛持久,能支撐你走很遠很遠。」
我拉住齊硯的衣袖,弱弱道:「可我不想恨,恨太累了,而且,我也沒打算走很遠很遠,因為我懶得走……」
就像曾經某日,他和我展示他用美人骨做的扇,道我若是害怕可以現在就逃回殷國。
我回道:「太累了,懶得動……」
活著便很辛苦了,若是還要分出精力去恨誰,實在太過勞累了。
齊硯眼底的陰鬱霎時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盈盈笑意和幾分無奈,「你啊……總有一日是懶死的。」
我點頭,「嗯,也不是不行。」
一旁的小翠都嘆了一聲。
殷韋最終被判了斬立決,齊硯替我拿的主意,說是既然我不敢殺人,就他來替我殺。
我的那些個兄弟姐妹都被發配到了邊疆,只有我三哥要去殷縣上任。
出發那日,他一步三回頭,很是不舍,「若是過得不順遂,定要寫信給我。」
我覺得好笑,「又不是此生都見不到了,哥哥這是做什麼?」
他似乎瞄了一眼齊硯,對我笑道:「你可拉倒,我若不主動來見你,以你的性子,肯定八百年都不會來看我。」
哦,這個確實。
最後是齊硯喚回出神的我:「杳杳,起風了,我們回去吧。」
12
一切塵埃落定後,還剩下一些流言,道是當年梁國敗得可惜,說梁氏姐弟是苦命人。
這都是老生常談,算不得什麼,只是不知從何時起,有人傳當今聖上非齊國皇室血脈,實乃冒名頂替之徒。
齊硯不曾與我說過這些,我都是從小翠和江寧瑤口中得知這些往事。
話說當年齊國與梁國還算是勢均力敵,齊國曾送一名皇子赴梁國,那便是齊硯。有人傳,其實當年的皇子早已遭到梁國毒手,死於非命,如今這個齊硯不過是一個頂替身份的無名小卒。
與此同時,還有人翻出齊硯的舊帳,稱其不是什麼仁君,相反的,其實他殘暴不仁,殺人如麻。梁氏後代近乎被絕,往年治理天下時也用過不少雷霆手段,害過不少無辜亡靈,還有早年送進宮的那些美人的家人也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,一遍遍哭訴自己女兒何等無辜可憐。
一時之間,民心大亂。
聽聞這幾日早朝,已有一些臣子進言,明里暗裡質疑齊硯的血統是否純正,說他們效忠的是齊家人,絕不許有人濫竽充數,魚目混珠。
齊硯卻毫無回應,只是一如既往地明面上寵著梁知意,半夜又翻窗戶來尋我。
我總覺得他瘦了不少,便在他吻我時避開他,輕聲道:「早些睡吧,你該多休息。」
他作亂的手就在我腰間停住,黑夜中他的眸子似乎在發光,「心疼我了?」
我假裝聽不出他話中的笑意,「嗯,怕你猝死了,我就沒有靠山了。」
他掐了把我的腰,「沒良心的。」
我不說話,只蹭了蹭他的胸膛。
半晌,他道:「杳杳,過幾日,隨我一起去秋獵好不好?」
表面是商量,實際是通知,我沒有拒絕的權力。
江寧瑤藉口要照顧咪咪和破抹布,不願一同過來,倒是在我出發前一日提醒我,要注意安全。
防的誰呢?自然是一同前往的梁知意。
自從殷國投降,梁知意便有些看不上我,不再像以往那樣攛掇我與她統一戰線。我倒是樂得她離我遠些,只是秋獵期間,我倆不得不打個照面。
「原先擔心皇后娘娘會傷心過度,還好看著氣色不錯。」
她笑盈盈的,但就是讓我不舒服,我敷衍答道:「本宮日日吃好睡好,自然氣色不錯。」
「是嗎?」她笑了下,又作憂愁狀,「嬪妾聽聞邊疆苦寒,不知娘娘的兄弟姐妹,是不是能吃好睡好。」
我打了個哈欠,「勞淑貴妃掛心,若是這麼擔心本宮的兄弟姐妹,不如哪日去邊疆親自看看。」
她臉色白了白,鄙夷地看了我一眼,不再說話。
我知她看不起我,也不指望她理解我。畢竟聽聞梁氏後代彼此之間關係親厚,她為族人鳴不平是正常的,但我又沒有那樣良善的族人,自然也就做不到她那樣臥薪嘗膽。
道不同,不相為謀。
齊硯瞧出我不願搭理梁知意,便提出帶我一同去狩獵。
可我懶得動,「我不會騎馬。」
他一臉意料之中,「我帶著你騎,又或者,你在這兒和淑貴妃一起等我回來。」
我:「我和你一起去……」
獵場是一片森林,青綠與金黃交錯,偶有落葉飄下,還有馬蹄踏下時的沙沙聲響,倘若忽略齊硯落在我後頸的吻,這一幕不失為難忘的美景。
我側了側身子,無語道:「齊硯,你不是出來打獵的嗎?都已經跑過去兩頭梅花鹿了!」
他笑了一聲,「不急。」隨後就是扯著韁繩,讓馬兒慢悠悠地走在林間,就像是,在等待著什麼。
良久,大約已是走到林深處,不知從何飛來一箭,驚得馬兒狂奔起來。
風在耳邊呼嘯,還有數不清的箭從四面八方破空而出,多數都被附近的暗衛擋下,少數漏過來的,也被齊硯避開。
他一手拉著韁繩,一手攬著我的腰,還笑得出來,「害怕嗎?」
我緊緊靠著他的胸膛,都不知此刻狂跳不止的,是我的心臟還是他的。
我聽到自己問:「我們會死嗎?」
齊硯輕笑,胸腔震動,「杳杳,你不會死的。」
是啊,我不會死的,因為射向我們的箭,最終,還是被齊硯接下了。
待馬兒中箭倒地,齊硯抱著我在地上翻滾數圈停下,我才發現他身上的異樣,後方已無追兵,但前方,也只有深不可測的密林,仿佛蒼茫天地之間,只剩下我與齊硯二人。
齊硯已經昏過去了,他身後的箭似乎早已被他自己折斷,只剩下一小段插著,因為身著玄衣,所以流出多少血都看不太出來。我也是恍然才發覺,草木香氣之中,還有那麼一股濃烈的血腥味。
他說,杳杳,你不會死的。
因為,他都幫我擋下了。
又或者,這些本就是衝著他來的。
「白痴。」
我把他狼狽的臉擦拭乾凈,又費力將他拖到隱蔽一點的地方靠到樹旁。
萬分慶幸,幼時我娘教過我野外的草藥,我憑著模糊的記憶力,在周圍找到了一些止血的藥草,隨後咬著牙將他後背的箭拔出,把嚼碎的草藥敷上,再撕下一段衣料替他包紮。
一番動作下來,我已是滿頭大汗,一半是他沉得慌,我要用很大的力氣搬動他,另一半,是我的心始終揪成一團,包紮時手都在微微顫抖。
最後我累極,靠在齊硯身旁睡了過去。
做了場怪夢,夢的最後齊硯對我露出悲涼的笑,再不言語。
醒來時已是傍晚,齊硯仍在昏迷。
太陽落山,林間有股陰濕的寒氣。我摸了摸齊硯的額頭,有薄薄的一層汗,冰涼涼的,頓時心下一沉,別無他法,只好面對面緊緊抱著他,再用他的外衣將我們兩人一同裹住,企圖渡些熱氣過去。
四周越來越暗,偶有鳥兒歸巢的厲聲,還有動物從灌木叢中穿梭而過的沙沙聲。
我又有些困意,但不敢睡,就一直在齊硯耳邊碎碎念,說的都是沒頭沒尾的東西。
「破抹布越來越大了,性格也變調皮了,他們都說破抹布長得不好看,可我覺得長得挺好看的,怎麼說,有種怪異的美。
「你和我說喜歡吃雞蛋羹是不是騙我的啊?我還給江寧瑤做過雞蛋羹,她說是最普通不過的雞蛋羹了。
「要我說,就怪你下午放跑了那兩隻梅花鹿,不然現在我們也不至於餓著肚子,現在烏漆嘛黑的,我晚上眼神也不好,從哪兒給你弄吃的呢?
「要是我們在農村就好了,我好歹還能給你偷點菜和雞蛋,這個林子又大又不好走,到時候餓死你也別怪我。
「你什麼時候能醒過來啊?以前都是你把我吵醒的,現在該換我吵醒你了,給個面子嘛……」
我囉里吧嗦說了一堆,最後聽見齊硯沙啞的聲音:「我都不知道,你原來話這麼多,吵得我頭疼。」
我歡喜地貼了貼他的額頭,確認他沒有發燒後嫌棄道:「你是背部中箭,要痛也應該是背痛。」
他悶悶地笑了,「怎麼不跑?」
我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他,「腦子也中箭了?」
他只笑,「我知當初你是被迫跟著我,如今我或許不再是皇帝,也就強迫不了你,若你想走,現在是最好的時機……嘶,你幹什麼?」
我咬了一口他的嘴,無語道:「想看看你的嘴巴到底有多硬。」
「殷嬈……」
我站了起來,打斷他,「說這麼多沒用的,還不如好好看看周圍,想想我們怎麼出去。」
他夜間視力也極佳,是唯一可指望得上的了。
齊硯沒動,仍看著我。
我很討厭他這副樣子,好像巴不得現在就被我拋棄,「你以為你很厲害嗎?想讓我幹嗎就幹嗎?我殷嬈真的不想做的事,誰都強迫不了我,你明不明白?而且就算我要走,那也要先回宮拿了東西,帶著破抹布一起走,你以為現在丟下你一走了之,我就能活得很好了嗎?齊硯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啊……」
什麼事都不與我說,擅自主張安排好一切,然後假惺惺說現在願意放我走,我雖然草包,但不至於這麼任人擺布。
「我不管你在下什麼大棋,與什麼人在做博弈,我出來前已經和江寧瑤還有小翠約好了,帶兩隻小兔子給她們玩,你是不是覺得你欠我很多啊?那你就按我的心意還我,先把我帶出這片狗屎林子,然後給我抓兩隻兔子,最後帶我回去!」
我說了好長一段話,仍覺得不解氣,話鋒一轉,「還是說你愛上了梁知意,所以想找個藉口放我走?齊硯你這個負心漢……」
情緒剛到位,齊硯就站起來抱住了我,順勢堵住了我喋喋不休的嘴。
林間,只剩下悉窣聲,和糾纏在一起的呼吸聲。
良久,他嘆道:「我真是怕了你了,一張小嘴這麼會說。」
我仍在氣頭上,撇開頭不想理他,又被他掰了過去。
「抱歉,我不趕你走了,」他溫聲道,「所以你也不許再說離開我的話。」
我:「我從來沒說過,是你自己瞎想出來的吧。」
他靜默了會兒,「好像是的。」
我:「……」
所以這人腦子裡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麼?
齊硯厚著臉皮貼上來,用鼻尖蹭我的臉,「那你也從沒說過不離開我。」
「我又不傻,你總是往梁知意宮裡跑,我幹嘛要說這種倒貼的話。」
他吃吃笑了,「醋了?」
我不想回答,轉移話題道:「你肩傷不疼了?」
他像是才想起來似的,浮誇地倒吸一口氣,「疼。」
我狐疑,「真有那麼疼?」
他點點頭,「嗯。」
我:「嘻嘻,你活該。」
13
打鬧結束,齊硯憑藉優秀的眼力和記憶力,帶著我走出了林子,並正巧遇上了尋我們的人。
也是在燈火下我才發現他臉色白得嚇人,看起來很虛弱,只怕之前的淡定都是裝的。
我霎時紅了眼,急得差點將隨行的太醫扛過來,齊硯卻安撫地拍了拍我的手,「沒事,我答應過你,會好好活著。」
那是好久以前的話了,我都差不多忘了。至此我揉了揉眼,只道:「那你不許反悔,你還要給我抓兔子呢。」
他慘白的唇勾出一抹笑,對旁人道:「讓皇后出去好好休息。」
我自己也確實憔悴不堪,聞言沒有抗拒,乖乖出去,吃飯洗漱,再好好地補了個覺。
醒來已是第二日,侍衛說太醫已經查看過了,除了肩傷,其餘並無大礙,眼下齊硯正在休息。
我不欲打擾他,便站在帷帳門前,問侍衛:「可查出是誰下的手嗎?」
齊硯曾告訴我,那日在天牢里的感覺叫恨,如今我算是再次體會到了。
大概齊硯下過旨,侍衛也沒瞞我,「是淑貴妃的人。」
梁氏姐弟,一個在獵場刺殺齊硯,一個在城內調兵遣將準備篡位。但齊硯大概將一切都算準了,刺殺沒有成功,篡位也沒有成功。昨晚齊硯出事的下一刻,二人就被抓了。
我都不免懷疑,齊硯肩上的傷是不是也是他計劃中的一環。
如此想著,我在給齊硯喂藥時,也就這麼問了。
他似乎也不意外,坦然點頭,「是,苦肉計。」
我:「……」
我理解不了,「為什麼?」
「想知道你愛不愛我。」他的手又緩緩攀上我的後頸,據我的經驗推斷,這表明他的一種掌控欲。
我只覺得白痴,「我若不愛你,會和你睡覺?」
齊硯想了想,「以你的性格,你覺得呢?」
我:「……」
可惡,被拿捏了。
齊硯繼續不緊不慢道:「還記得我以前教你的嗎?那叫恨意,你說太辛苦。所以現在我教你別的,杳杳,你昨晚對我的那番表露,叫愛意。」
我看到了他眼底的執拗與瘋狂,突然明白了些什麼,「若我昨晚決定拋下你獨自離開,我是不是會死?」
齊硯默認了,「還記得我給你看的用美人骨做的扇子嗎?雖然從來沒在你面前殺過人,但我其實不是個好人,在你不知道的角落,我殺了無數人。所以我想,也可以殺了我的心上人。我的真面目就是這樣,殷嬈。」
我思索半晌,感嘆道:「那你挺變態的。」
齊硯:「……」
齊硯扯了扯嘴角,「除此之外,你沒有別的想法嗎?」
我點點頭,「你快點好起來,還欠我兩隻兔子呢。」
齊硯不說話了,只盯著我看,看得我渾身發毛,最後硬著頭皮上前吻了吻他的嘴角,皺巴了臉,「好苦。」
他倏地笑了,按著我的後腦勺深入,末了才笑道:「這樣才能嘗出來,良藥苦口。」
我瞪了他一眼,「流氓。」
待齊硯傷恢復了大半,我們一行人回了皇宮,順帶還有兩隻兔子。
最後江寧瑤與我大眼瞪大眼,提議道:「今晚吃紅燒兔頭吧?」
我覺得甚妙。
此前的事都已被查了個水落石出。此次刺殺,以及之前宮宴上樑知意擋的那一刀,都是梁志敏的人做的。這期間梁志敏還有私底下招兵買馬、圖謀不軌、結黨營私等罪行。梁知意使用迷情香的事也被曝了出來,以及與前朝私通、擾亂朝政等。總之這對姐弟,一夜之間,聲名狼藉,雙雙入獄。
行刑前一夜,梁知意求見我,我犯懶,齊硯卻要帶著我一起過去。
梁知意仍舊挺直脊樑,面上不再一副溫婉神情。
「你怎麼敢一起來的?」她對著齊硯恨恨道。
齊硯擁著我,懶懶道:「你不就是想與她說我的事嗎?那我這個當事人,為何不能在場?」
我不喜歡這種打謎語的對話,「有事說事,沒事我走了。」
還和江寧瑤約好了今晚吃紅燒豬蹄呢。
梁知意一臉「你真可悲」的表情,「你知不知道你身邊是個什麼樣的男人?」
我即答:「一個變態。」
然後齊硯掐了一把我的腰。
我順勢推開他,「你出去,我和她說悄悄話。」
齊硯:「……」
梁知意:「……」
我坐在梁知意對面,撐著頭道:「好了, 你想和我說什麼?」
想說什麼呢?不過是一些陳年舊事罷了。
齊硯確實不是當年那個皇子,他是隨著皇子一同前來的小太監。至於梁知意為何這麼確定,是因為那個皇子就是梁國人殺的。誰都沒想到後來那個小太監冒名頂替,成了齊硯。
我抹了把臉,不太相信,「你確定是小太監?不是什么小侍衛之類的?」
「當然……你什麼意思?」
我摸了摸下巴,「額……據我所知,齊硯不是太監。」
梁知意瞬間瞳孔地震,過了會兒苦笑,「難怪, 我還以為那香對他沒作用是因為他是太監……原來如此,原來如此……」頓了頓, 又問我, 「他殺了你父親,你怎麼還做得到和他待在一起?」
我不想解釋太多,「每個人的境遇不同, 你不應該用你的想法綁架我。若你想告訴我的就是齊硯的身份,那我覺得到這裡就差不多了。」
正欲起身離開, 梁知意又叫住我:「你不覺得這樣一個人很可怕嗎?作為你的枕邊人, 心機如此之重。」
我贊同地點點頭,「是挺可怕的。」
「那你為什麼不離開他?」
我應得理所當然, 「懶得跑……」
那晚齊硯難得只抱著我睡,其他什麼也沒幹。他與我說其實他也是齊國皇子, 但是一個宮女所生,極不得寵。當年只有那個皇子對他好, 所以他喬裝打扮隨他一起去了梁國。不承想遭此不幸,為了報仇,他不得不冒名頂替, 而後大力發展齊國,一舉吞併了梁國。
我不得不感嘆:「好勵志的故事。」
齊硯:「……」
齊硯蹭了蹭我的頸間,「你沒有別的想說的?」
「哦,是有。」我這才想起什麼,「江寧瑤要我求求你, 放她出宮去。」
原來齊硯留她下來,只是為了陪我解解悶,如今他已經處理好了梁國的事, 江寧瑤也覺得宮裡太無聊了,就想出去了。
「這是小事, 」齊硯吻了吻我的脖子, 「你還有別的要說嗎?」
我想了想,「該睡覺了?」
齊硯氣得咬了我一口。
我笑了,「好啦,提問, 為什麼殷嬈不離開齊硯這個變態呢?」
在那一瞬間齊硯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。
我回抱住他,在他耳邊小聲道:「因為她學會了愛意。」
恨意太累人了,還是愛你比較容易。
 喬峰傳 • 18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18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740次觀看
奚芝厚 • 740次觀看 花伊風 • 1K次觀看
花伊風 • 1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66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66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1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10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83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83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1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1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95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95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77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77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開心果 • 760次觀看
開心果 • 76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1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1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7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700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40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40次觀看 花伊風 • 180次觀看
花伊風 • 18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33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33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41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41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74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74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4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40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32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32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5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50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56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560次觀看 花伊風 • 570次觀看
花伊風 • 570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