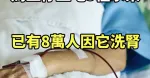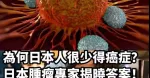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遲遲完整後續

3/3
當初養它,它還很小,小馳兩隻手就可以捧起來,它被裴延禮丟掉的那天,小馳什麼都沒說,可第二天的枕頭上卻是濕漉漉的。
看見圓圓就像是又看到了小馳。
我克制不住激動,拍著玻璃,驚動了寵物店的人,他衝上來推開我,我像是發了瘋,指著那隻貓說是我的。
店員大概以為我是瘋子,推搡著要將我趕出去。
我不是瘋子,我只是太激動。
失而復得的激動。
小馳的圓圓又找到了,那我還可以見到小馳嗎?
可來接圓圓的不是小馳,是梁平霜。
她從寵物店外走過來,與我的眼睛對上,又看了看那隻貓,「唐枝……你喜歡鈴鐺嗎?」
小貓被抱了出來,我親眼看著我的丈夫被梁平霜搶走,又看著小馳的貓趴在她懷裡,跟她親近。
「我們鈴鐺可乖了,你要摸摸它嗎?」
鈴鐺。
它不叫圓圓了,可它就是圓圓,我記得。
我突然上手去搶貓,嚇壞了梁平霜,她連忙後退,「唐枝,你幹什麼?搶東西搶習慣了是嗎?」
「它是小馳的貓,不是你的!」我情緒崩潰,胃腹絞痛,大聲喊著。
梁平霜一副看笑話的樣子,「唐枝,這可是延禮送給我的,怎麼就成你的了?你霸占他那麼多年還不夠,現在連一隻貓也要搶?」
是裴延禮。
是他拿了小馳的貓給梁平霜。
他憑什麼?!
就算他恨我,可小馳無辜。
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,我的東西,裴延禮都會送給梁平霜?
大約是他的生日開始。
梁平霜出現後,裴延禮的眼神便跟隨著她,她優秀耀眼,與裴延禮天生一對,裴延禮會因為過生日因為等不到她的禮物而難過。
那天坐在台階上,裴延禮失落望著月亮,年少的他五官俊朗,清薄的月色落在他臉上,照出他眼眶裡的空洞黯淡。
他問我:「唐枝,你說她是不是不記得我的生日?」
他是在說梁平霜。
我掩藏了自己的落寞,將打工攢錢買給裴延禮的手錶送給他,苦笑著說,「興許她是忙,這個送給你。」
裴延禮接過去,看都沒看。
第二天他去接我,梁平霜同行,我看到我的那塊表,戴在了她的手腕上,此後還有許多,比如裴叔叔派給我的司機,被裴延禮叫去接梁平霜,梁平霜要參加比賽,裴延禮拿了我的設計稿圖給她,再到後來,是出國名額。
那天他站在我面前,坦坦蕩蕩,不夾雜半分心虛,「唐枝,平霜比你更需要出國,她很有才華不應該埋沒。」
同一天。
母親被查出胃癌,命不久矣,她希望裴延禮帶著我出國,這是她的遺願,梁平霜連她的遺願都搶走了。
我忍不住坐在母親的床頭哭泣了一整晚,不知是在哭失去的出國名額,還是在哭即將離世的母親,又或者是裴延禮的絕情。
彼時我沒當母親,不知道在一個母親眼裡,孩子的眼淚是怎樣的致命武器,甚至可以讓我那位一輩子碌碌無為,老實本分的母親去設計裴延禮。
在裴延禮與梁平霜出國的前一晚,我與他睡在了一張床上,我明白母親的良苦用心,他怕裴延禮娶了梁平霜,怕我在裴家沒有立足之地,怕她走後我無依無靠。
如果我早知那杯酒有問題,我是不會喝下去的,可裴延禮不信,他在酒店的床上掐著我的脖子,質問我不是跟賀儀光在一起了,又爬他的床,是什麼意思?
我說我不知情。
他笑了,笑得痛快,手上的力氣不斷加緊,言語如一把利刃,撕開了我的胸腔,「你跟你母親一樣,天生就是吸血鬼。」
9
那是母親生命最後倒數的幾天,我帶著一臉的傷痕去找她,我指責她,責怪她,我親口問她:「您跟裴叔叔,是什麼關係?」
她漲白了臉,氧氣面罩中的白色哈氣一層一層,聲音又啞又沉,「是誰……跟你說的。」
「裴延禮。」我再次流了淚,我哭著告訴她,「他說,當媽的成不了,就換我這個做女兒的。」
母親僵硬地搖頭。
我哭著說,「媽媽,現在我該怎麼辦?」
那是我跟她說的最後一句話,見的最後一面,夢裡我跪在母親墳前,跟她說我錯了,回應我的,卻是一雙柔軟,溫熱的,沾染著小孩子氣味的手。
是小馳,可一轉眼,他的手變冷了,身子也僵硬了,我抱著他號啕大哭,無措地大喊:「有沒有人……有沒有人救救我的孩子?」
沒有人可以救他。
我就那麼眼睜睜地看著他在我懷中咽氣。
在夢裡,我的眼淚流了下來。
後來我才知道,母親與裴父差點在一起,可後來她得了病,又得知我對裴延禮的心思,想要成全我們。
可那時,裴延禮身邊有了梁平霜。
她是為了我,才擔了這個罵名,哪怕走之前惡毒一回,也要保我衣食無憂的錦繡前程。
可我讓她失望了。
我沒保住裴太太的身份,沒保住自己的孩子,還患上了跟她一樣的病。
等待太漫長,過去在這裡,我就是如此,日復一日等著裴延禮歸家,可這次怎麼才過半個鐘頭,就已經疲倦了。
生命仿佛在流逝,照這個速度下去,不知熬不熬得到聖誕節,往年小馳是最喜歡聖誕節的。
今年的聖誕禮物,是圓圓。
為了圓圓,我不惜親自找過來,要見裴延禮一面。
10
裴延禮來時我等在老宅樓下,面色慘白如紙,他擰著眉走來,語調中竟然多了溫柔,「怎麼不回房間休息,臉色這麼差,胃病還沒好些嗎?」
什麼胃病,是癌症。
是好不了的。
我躲開了他往我額頭探的手,「不用,我來是想問你,是你把圓圓送給梁平霜的?」
「什麼圓圓?」
他不知道小馳的貓叫什麼,擅自送給了梁平霜,又改名叫鈴鐺。
我笑不出來,哭不出來,唯有平靜面對,「小馳的貓,那是他的。」
裴延禮眼眸很是複雜,他抬手過來,輕撫著我的面龐,表情里的歉意我無法忽視,「我們先上樓,貓的事改天再說。」
我哪還有改天?
「我只要小馳的貓。」我的聲音控制不住拔高,氣一上來,就忍不住想要咳嗽,弓著腰,面部充血,咳得眼前昏花。
裴延禮替我拍背順氣,我將他的手揮開,表情急迫。
「你別急,我現在就打電話要。」他拿出手機,望了眼什麼都沒有的茶几,不滿喊道:「怎麼沒人倒杯水,都死了嗎?!」
真難得,他還會在乎我有沒有水喝。
在旁打完了那個電話,我等待著裴延禮的答覆。
他走過來,義正詞嚴,「我會把圓圓拿回來給你的,你在這裡等我好嗎?」
抓住時機,我又道出了另一件正事,「你可以把離婚後屬於我的那部分錢給我嗎?我現在很需要錢。」
我要還給賀儀光,他不是什麼富裕人家的孩子,這些天給我花的錢占了太多,我是要還給他的。
沒什麼比輕輕鬆鬆地走更好。
「你來這裡,是拜託我找貓,還是要錢的。」
我說:「都有。」
他神色頓時複雜了很多,拖著虛弱的身體,從床頭的皮夾中拿出一張卡,遞給了我,「密碼,小馳生日。」
原來他是記得小馳生日的,記得這個日子,卻從不出現。
我接過卡,他卻沒有鬆手,「錢我給你,但不是什麼離婚補償。」
裴延禮接著鄭重其事,「唐枝,你等我回來,我去把小馳的貓找回來,我們重新開始,小馳的房間我重新布置過,生日我們下次一起陪他過,好不好?」
可我等不到小馳的下一次生日了啊。
他為什麼不可以早一點,早一點答應陪小馳過生日?
太晚了。
裴延禮真的太晚了。
這一等好像等了一輩子那麼長久。
在被病痛折磨著時,我望著裴家老宅,想起第一次我跟母親走進這裡,裴延禮還是一副少年模樣,後來我們在這裡結婚,穿著婚紗那晚,我什麼都沒等到。
緊接著母親去世,我在我與裴延禮的新房裡哭泣,他嫌我煩,將我扔了出去。
懷著小馳時那段日子我始終沉浸在悲痛中,發現懷孕已經很晚了,早已過了可以進行手術的時間。
那幾個月里,裴延禮不止一次勸我引產,他真的討厭極了這個孩子。
我不答應,我一點點將小馳養大,一個人帶他打針吃藥,為他穿衣暖身,哄他入睡沉眠,他掉一滴淚我心碎,他一笑我再沒煩惱。
小馳知道爸爸不愛他,也不愛我。
為了讓我可以多得到一點愛,他弄傷自己,多次讓自己感冒發燒,就為了讓裴延禮回來看望我們母子。
可這不是我要的。
我只要我的小馳好,我曾輕聲細語告訴他,我不要他傷害自己,沒什麼比他更重要,何況欺瞞撒謊是不對的。
可小馳不聽,他只是個孩子,他只想讓爸爸媽媽在一起。
很快,裴延禮發現了,這一招也失去了作用,直到小馳的死訊傳到他耳邊,他都以為是小馳跟他開的玩笑。
在這座房子裡,我遇見了裴延禮,失去了母親,有了孩子,又失去了孩子。
或許是真的走到盡頭了。
這些過往走馬觀花出現在腦海里。
裴延禮是凌晨回來的。
他懷裡擁著一隻通體雪白的小貓,拿著小貓的爪子碰觸我的鼻尖,「小枝,你要的圓圓,我給你找回來了。」
是圓圓嗎?
我快要看不清了。
伸手接貓時頓了下,認出了這隻貓不一樣的瞳孔顏色,耳朵上的顏色是一樣的,大小也差不多,可就是不一樣。
是直覺。
「怎麼了?」裴延禮問我,他讓那隻貓在自己懷裡躺著,自顧自道:「以前小馳小,我總覺得養寵物會傷了他,到時候你又要心疼,所以不答應讓他養。」
我垂下了手,不打算抱貓了。
這不是圓圓,為什麼要找一隻假圓圓騙我,要是小馳知道,一定會怪我。
「裴延禮,這個時候了,你沒必要騙我的。」
在這裡,我等了一輩子。
最後卻連小馳的一隻貓都沒等到。
裴延禮怔了下,「騙你什麼?」
「這不是圓圓?」我太過冷靜,冷靜到篤定,「圓圓呢?」
他真的去找梁平霜要了,細看之下,他面上還有巴掌印,領口有些褶皺了,大概是兩人發生了爭執,回來時很焦急疲憊,但還是拿貓在哄我。
「圓圓墜樓了。」
就在裴延禮打了電話後的半小時里。
梁平霜是兇手,但沒人可以懲戒她。
我又痛又悲,但麻木了,「我要走了。」
「你要去哪兒?」裴延禮讓貓從自己懷裡溜走,空出手來,那樣子像是請求,可他請求我什麼?
「回家。」
全身的力氣被抽空了,我眼前一黑,腿軟倒下,最後嘴巴里還在呢喃著三個字:「找小馳。」
可還沒等我找到他,便在裴延禮眼前暈了過去。
11
好吵。
是誰在敲門,在喊我的名字?
拼盡全力想要保持清醒,可混混沌沌的思緒里只有很淡的吵聲,像是殘缺的片段,像是有男人在吼叫,在砸東西。
家庭醫生的衣領被揪起來。
「她是我的妻子,她病了,為什麼不告訴我?」
我看到了。
那是裴家的家庭醫生,站在他身邊的是一臉漠然的賀儀光,他反問裴延禮,「她是你的妻子,她快死了,你才知道她得胃癌了嗎?」
「裴先生,請你冷靜。」
家庭醫生竭力在維護場面,「兩個月多前,我給你打過一通電話,是您親口說,唐小姐的事情跟你無關。」
原來,他早該知道啊。
我遲緩地呼出一口氣,氧氣面罩壓在我的臉上,呼吸聲像是我的倒計時,每一口氣都是艱難而珍貴的。
裴延禮走過來,在死前,我親眼看到了那麼驕傲的男人在我面前低下頭,他想要去拉我的手,又怕弄疼了我,手抬在空中,遲遲沒有放下,像是一個弄壞了心愛的玩具,竭力想要彌補拼湊,卻不知從何下手的小孩子。
片刻。
他捂住了自己的臉,隱隱約約,我聽見他嗚咽的哭聲在病房響徹。
真吵。
可不可以離我遠點?
可惜我開不了口,罵不了人。
不知過去多久。
賀醫生走了過來,我眼皮動了動,看到他白色的影子站在裴延禮身後,「你這樣會吵到她。」
「滾開。」裴延禮壓著顫音在吼,嗓音是嘶啞乾裂的。
他哭了很久。
哭得我都要煩了,我曾以為我的眼淚最多,沒想到他也會流淚,還是為我。
「人都要死了才知道後悔,當初幹什麼去了,她是你的妻子,這麼多年來,你關心過她嗎?」賀儀光一字一句,如針扎心,「以前你懷疑我們,結了婚你還是懷疑,可你有沒有想過,她就只是想當你的妻子而已。」
「我為唐枝不值。」
「我沒想到她會生病,真的,我沒想到。」
醫院裡到處都是重症病人。
他們吃不下東西,靠著藥丸子度日,咳血是最輕的,掏心抽血的疼是每天都要承受上百遍的,這些裴延禮怎麼會知道?
他只當我是為小馳的死在胡鬧,在小題大做,他以為,我還會回去。
他們在我床邊爭吵,絲毫不在意我是個將死之人。
裴延禮輕輕將我的手掖進被褥里,背對著賀儀光,「你不是醫生嗎?你可以救活小枝嗎?」
「她早就不想活了,誰都救不了了。」
到了這個程度,賀儀光說的是真話。
裴延禮:「你出去。」
屋子安靜了下來。
身體的知覺很虛幻,我的手被抬了起來,貼在裴延禮的臉頰上,他親吻我的掌心,有眼淚在往下落,「為什麼不告訴我你生了病?」
「因為小馳走了,你連病都不治了?」
「那我怎麼辦,你心裡只有那個小孩子,分給過一點位置給我嗎?」裴延禮用我軟趴趴的手打自己的臉,「是我不對,我怎麼可以吃小馳的醋,怎麼會去吃賀儀光的醋?」
「我們才是夫妻。」
「小枝。」
「你醒來打我,你想怎麼罵我打我,我都願意。」
他在喚我的名字,我聽得到。
好想掙脫他的手,只因我看到了小馳在向我招手,他在叫媽媽,他說:「媽媽,這裡好黑,我好害怕。」
想衝過去擁抱他。
裴延禮的手卻死死扯著我。
怎麼這個時候,他還不肯放過我?
12
有針扎進我的皮膚里,疼得我蹙緊了眉頭,腳趾跟著蜷縮了下,骨頭縫裡好似都在疼。
藥物輸進我的身體里,疼痛短暫消失了,生命中的疼卻是藥物無法撫平的。
床頭有人在忙碌。
是醫生,是護士,焦急的吵聲伴在耳畔。
心電圖上的生命體徵很微弱了,在瀕死之際,我好像又看到了小馳,他坐在一片柔軟的草地上,小小的身子趴在草里,一抬頭,那張軟軟的小臉上生著一對酒窩,一笑眉毛彎彎。
他甜甜地叫我媽媽,我想要去抱住他,可耳邊還有人在叫我,叫我的名字。
場景變得扭曲,裴延禮的臉出現在我眼前,他在呼喚我的名字,可我想要跟小馳走,我想說停下吧,就這樣離開,是我最後的夙願。
可他沒有停。
這些天他找來了最好的醫生救我的命,可再好的藥對我都沒用了,我沒有了求生的意志,意識都在跟著夢中的小馳走。
可現實里,裴延禮死死拽著我,不讓我走。
直到心電圖上的有了波動。
是他將我救了回來。
他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,我這條命是他的,要我惜命。
我在醫院躺了一周,這一周里,裴延禮寸步不離守在我身邊。
可我知道,我撐不下去了。
在生命盡頭,我卻看到了我最不想要見到的人。
聖誕前夕。
梁平霜站在我的床邊,我這個樣子,她一定很痛快,她觀賞著我的慘狀,將我的醜陋與病態盡收眼底。
可她卻說,「真是報應。」
接著她又補了句,「是裴延禮的報應,這麼多年他耍我,利用我,讓我對他死心塌地,最後卻告訴我,他從沒愛過我,就連送我的貓都要拿走,憑什麼?」
耳邊的聲音斷斷續續,一句接著一句,砸進我死水一潭的心中。
原來到最後,我們誰都沒有得償所願。
「唐枝,你一定很納悶,為什麼他會恨你的孩子。」
梁平霜低頭覆身,側在我耳邊,在我還有呼吸時,給我致命一擊,「因為他以為,那是你跟賀儀光的孩子,是我告訴他的,是我假造了親子鑑定書,他就信了。」
大笑幾聲。
她身子都在顫,眼角卻擠出淚花,「他真的就信了!」
胸腔里在劇烈跳動著,我已經分不出那究竟是憤怒還是其他了,梁平霜卻還沒停止,「你知道嗎?你的孩子死的時候,裴延禮這個親生父親竟然是慶幸的,他以為這個孩子死了,就能跟你重新開始了!」
他以為的開始,殊不知卻是結束。
撐著沉重的眼皮,我半睜開眸,活動手指,第一眼看到的是從外面走進來的裴延禮,他提著梁平霜的胳膊讓她滾。
梁平霜一聲聲嘶吼著,「裴延禮,你活該,活該!」
他是活該。
我更是。
梁平霜來後裴延禮大發雷霆,他罵了很多人,像是無力的宣洩,他想要喂我喝水,可唯有他喂的我不喝。
只好護士來喂。
他在旁看著,等護士走了,想要替我擦拭嘴角,我側過臉去,看著窗戶外的飄雪,虛無地張了張嘴巴,「快聖誕了吧?」
裴延禮:「是,明天聖誕節,我們一起過節?」
我要熬到那一天,去見我的小馳。
「小枝,我會治好你的。」裴延禮強行握住我的手,他想要撫平上面的針孔,卻做不到,「我早應該知道的,你瘦了那麼多,臉色那麼差,我怎麼沒發現你病了?」
他是沒發現。
可我告訴過他的。
我是說了的。
那天,我問了一句:「最近胃裡總疼,要是絕症可怎麼辦?」
裴延禮聽了只是放下筷子,「那不要死在這裡,太晦氣。」
現在真的是絕症了,他難道不覺得晦氣嗎?
13
聖誕節的夜晚總是熱鬧繁華的。
聖誕樹很漂亮,綠色的,佇立在商場中央,掛著許多裝飾物,路過的行人大多都會停下拍照,彩燈打開閃爍著、將每張笑臉都照亮。
我坐在車裡,裹著厚重的衣物,帽子遮住了眉毛,只留在外一雙眼睛,隔著車窗,望著聖誕的夜晚。
下雪了。
雪花是白的,很純凈,像是小馳的眼睛。
是微笑著的,也是失落的。
那一次也是在這裡,我抱著小馳坐在車裡,他指著那棵聖誕樹說漂亮,我跟他一同看去,看到了樹下站著裴延禮與梁平霜。
他們在那裡合照。
我心一緊,忙捂住了小馳的眼睛。
在茫茫雪霧中,我好像看見了小馳正穿著紅色的毛衣坐在樹下,他摸著聖誕樹上的小鈴鐺,「媽媽,這個好漂亮。」
是很漂亮。
可小馳的笑臉不見了,取而代之的是裴延禮焦急的面色,手臂圈著我的肩膀,讓我靠在他懷裡。
「小枝。」
我好冷,他想要給我溫暖,可他忘記了,自己就是一塊冰,「要不要下去走走?」
我搖頭,只遠遠地瞧上一眼,就當作是替小馳過這個聖誕了。
雪還在下。
力氣在減少。
裴延禮好像感受到了我體溫在下降, 緊接著搓著我的手腕,可上面大片大片的淤青,全是扎針留下,「小枝,你是不是冷?你跟我說句話好不好?」
他臉頰貼著我的額頭,還是那股子清冽乾淨的氣味,卻讓我覺得好遙遠,遠得像是上輩子的事情。
這些年,他留給我的氣味大都是梁平霜身上的香味。
坐在車裡,他跟我一起賞雪, 下巴摩挲著我的頭髮,車廂中很安靜溫暖, 風雪被隔絕在外, 我與他一起看雪。
他的聲音如絮,很輕地飄在我耳邊,「小枝, 你還記得那年我為什麼不解釋我跟你的事情嗎?」
「我應該告訴你的,這麼多年, 我分明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告訴你的。」
雪勢變大了, 小馳在那邊冷不冷?
沒關係。
我很快就要見到小馳了。
畢竟這是小馳的最後一項心愿:永遠跟媽媽在一起。
眼皮上像是凝結了一層霜,我合上眼眸, 原來人在最終失去的是聽覺,靈魂像是脫離了身體, 可裴延禮的話還在繼續,「小枝, 如果不是爸爸告訴我他要娶你媽媽,如果不是他讓我把你當作妹妹,我們不該是這樣的結局。」
「你說是不是?」
「小枝?」
「小枝, 你很冷嗎?」
「小枝,你等等我。」
我不等了他,我要離他遠遠的,下輩子,下下輩子, 都不要再見到這個人。
聲音變得好遠好遠。
好像有哭聲,有人在叫我。
光變得很微弱了。
在我的視線中,擴大、又縮小。
我很累。
眼皮很沉, 抬不起手,想要抱一抱小馳, 捕捉到的卻是一團影子, 我一直追一直追,哭喊著、奔跑著、一直走到盡頭。
大汗淋漓,氣喘吁吁,終於看到了小馳。
他懷裡抱著雪白的圓圓, 「媽媽,你來了?」
這一次,我終於抓住了小馳的手。
(全文完)
看見圓圓就像是又看到了小馳。
我克制不住激動,拍著玻璃,驚動了寵物店的人,他衝上來推開我,我像是發了瘋,指著那隻貓說是我的。
店員大概以為我是瘋子,推搡著要將我趕出去。
我不是瘋子,我只是太激動。
失而復得的激動。
小馳的圓圓又找到了,那我還可以見到小馳嗎?
可來接圓圓的不是小馳,是梁平霜。
她從寵物店外走過來,與我的眼睛對上,又看了看那隻貓,「唐枝……你喜歡鈴鐺嗎?」
小貓被抱了出來,我親眼看著我的丈夫被梁平霜搶走,又看著小馳的貓趴在她懷裡,跟她親近。
「我們鈴鐺可乖了,你要摸摸它嗎?」
鈴鐺。
它不叫圓圓了,可它就是圓圓,我記得。
我突然上手去搶貓,嚇壞了梁平霜,她連忙後退,「唐枝,你幹什麼?搶東西搶習慣了是嗎?」
「它是小馳的貓,不是你的!」我情緒崩潰,胃腹絞痛,大聲喊著。
梁平霜一副看笑話的樣子,「唐枝,這可是延禮送給我的,怎麼就成你的了?你霸占他那麼多年還不夠,現在連一隻貓也要搶?」
是裴延禮。
是他拿了小馳的貓給梁平霜。
他憑什麼?!
就算他恨我,可小馳無辜。
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,我的東西,裴延禮都會送給梁平霜?
大約是他的生日開始。
梁平霜出現後,裴延禮的眼神便跟隨著她,她優秀耀眼,與裴延禮天生一對,裴延禮會因為過生日因為等不到她的禮物而難過。
那天坐在台階上,裴延禮失落望著月亮,年少的他五官俊朗,清薄的月色落在他臉上,照出他眼眶裡的空洞黯淡。
他問我:「唐枝,你說她是不是不記得我的生日?」
他是在說梁平霜。
我掩藏了自己的落寞,將打工攢錢買給裴延禮的手錶送給他,苦笑著說,「興許她是忙,這個送給你。」
裴延禮接過去,看都沒看。
第二天他去接我,梁平霜同行,我看到我的那塊表,戴在了她的手腕上,此後還有許多,比如裴叔叔派給我的司機,被裴延禮叫去接梁平霜,梁平霜要參加比賽,裴延禮拿了我的設計稿圖給她,再到後來,是出國名額。
那天他站在我面前,坦坦蕩蕩,不夾雜半分心虛,「唐枝,平霜比你更需要出國,她很有才華不應該埋沒。」
同一天。
母親被查出胃癌,命不久矣,她希望裴延禮帶著我出國,這是她的遺願,梁平霜連她的遺願都搶走了。
我忍不住坐在母親的床頭哭泣了一整晚,不知是在哭失去的出國名額,還是在哭即將離世的母親,又或者是裴延禮的絕情。
彼時我沒當母親,不知道在一個母親眼裡,孩子的眼淚是怎樣的致命武器,甚至可以讓我那位一輩子碌碌無為,老實本分的母親去設計裴延禮。
在裴延禮與梁平霜出國的前一晚,我與他睡在了一張床上,我明白母親的良苦用心,他怕裴延禮娶了梁平霜,怕我在裴家沒有立足之地,怕她走後我無依無靠。
如果我早知那杯酒有問題,我是不會喝下去的,可裴延禮不信,他在酒店的床上掐著我的脖子,質問我不是跟賀儀光在一起了,又爬他的床,是什麼意思?
我說我不知情。
他笑了,笑得痛快,手上的力氣不斷加緊,言語如一把利刃,撕開了我的胸腔,「你跟你母親一樣,天生就是吸血鬼。」
9
那是母親生命最後倒數的幾天,我帶著一臉的傷痕去找她,我指責她,責怪她,我親口問她:「您跟裴叔叔,是什麼關係?」
她漲白了臉,氧氣面罩中的白色哈氣一層一層,聲音又啞又沉,「是誰……跟你說的。」
「裴延禮。」我再次流了淚,我哭著告訴她,「他說,當媽的成不了,就換我這個做女兒的。」
母親僵硬地搖頭。
我哭著說,「媽媽,現在我該怎麼辦?」
那是我跟她說的最後一句話,見的最後一面,夢裡我跪在母親墳前,跟她說我錯了,回應我的,卻是一雙柔軟,溫熱的,沾染著小孩子氣味的手。
是小馳,可一轉眼,他的手變冷了,身子也僵硬了,我抱著他號啕大哭,無措地大喊:「有沒有人……有沒有人救救我的孩子?」
沒有人可以救他。
我就那麼眼睜睜地看著他在我懷中咽氣。
在夢裡,我的眼淚流了下來。
後來我才知道,母親與裴父差點在一起,可後來她得了病,又得知我對裴延禮的心思,想要成全我們。
可那時,裴延禮身邊有了梁平霜。
她是為了我,才擔了這個罵名,哪怕走之前惡毒一回,也要保我衣食無憂的錦繡前程。
可我讓她失望了。
我沒保住裴太太的身份,沒保住自己的孩子,還患上了跟她一樣的病。
等待太漫長,過去在這裡,我就是如此,日復一日等著裴延禮歸家,可這次怎麼才過半個鐘頭,就已經疲倦了。
生命仿佛在流逝,照這個速度下去,不知熬不熬得到聖誕節,往年小馳是最喜歡聖誕節的。
今年的聖誕禮物,是圓圓。
為了圓圓,我不惜親自找過來,要見裴延禮一面。
10
裴延禮來時我等在老宅樓下,面色慘白如紙,他擰著眉走來,語調中竟然多了溫柔,「怎麼不回房間休息,臉色這麼差,胃病還沒好些嗎?」
什麼胃病,是癌症。
是好不了的。
我躲開了他往我額頭探的手,「不用,我來是想問你,是你把圓圓送給梁平霜的?」
「什麼圓圓?」
他不知道小馳的貓叫什麼,擅自送給了梁平霜,又改名叫鈴鐺。
我笑不出來,哭不出來,唯有平靜面對,「小馳的貓,那是他的。」
裴延禮眼眸很是複雜,他抬手過來,輕撫著我的面龐,表情里的歉意我無法忽視,「我們先上樓,貓的事改天再說。」
我哪還有改天?
「我只要小馳的貓。」我的聲音控制不住拔高,氣一上來,就忍不住想要咳嗽,弓著腰,面部充血,咳得眼前昏花。
裴延禮替我拍背順氣,我將他的手揮開,表情急迫。
「你別急,我現在就打電話要。」他拿出手機,望了眼什麼都沒有的茶几,不滿喊道:「怎麼沒人倒杯水,都死了嗎?!」
真難得,他還會在乎我有沒有水喝。
在旁打完了那個電話,我等待著裴延禮的答覆。
他走過來,義正詞嚴,「我會把圓圓拿回來給你的,你在這裡等我好嗎?」
抓住時機,我又道出了另一件正事,「你可以把離婚後屬於我的那部分錢給我嗎?我現在很需要錢。」
我要還給賀儀光,他不是什麼富裕人家的孩子,這些天給我花的錢占了太多,我是要還給他的。
沒什麼比輕輕鬆鬆地走更好。
「你來這裡,是拜託我找貓,還是要錢的。」
我說:「都有。」
他神色頓時複雜了很多,拖著虛弱的身體,從床頭的皮夾中拿出一張卡,遞給了我,「密碼,小馳生日。」
原來他是記得小馳生日的,記得這個日子,卻從不出現。
我接過卡,他卻沒有鬆手,「錢我給你,但不是什麼離婚補償。」
裴延禮接著鄭重其事,「唐枝,你等我回來,我去把小馳的貓找回來,我們重新開始,小馳的房間我重新布置過,生日我們下次一起陪他過,好不好?」
可我等不到小馳的下一次生日了啊。
他為什麼不可以早一點,早一點答應陪小馳過生日?
太晚了。
裴延禮真的太晚了。
這一等好像等了一輩子那麼長久。
在被病痛折磨著時,我望著裴家老宅,想起第一次我跟母親走進這裡,裴延禮還是一副少年模樣,後來我們在這裡結婚,穿著婚紗那晚,我什麼都沒等到。
緊接著母親去世,我在我與裴延禮的新房裡哭泣,他嫌我煩,將我扔了出去。
懷著小馳時那段日子我始終沉浸在悲痛中,發現懷孕已經很晚了,早已過了可以進行手術的時間。
那幾個月里,裴延禮不止一次勸我引產,他真的討厭極了這個孩子。
我不答應,我一點點將小馳養大,一個人帶他打針吃藥,為他穿衣暖身,哄他入睡沉眠,他掉一滴淚我心碎,他一笑我再沒煩惱。
小馳知道爸爸不愛他,也不愛我。
為了讓我可以多得到一點愛,他弄傷自己,多次讓自己感冒發燒,就為了讓裴延禮回來看望我們母子。
可這不是我要的。
我只要我的小馳好,我曾輕聲細語告訴他,我不要他傷害自己,沒什麼比他更重要,何況欺瞞撒謊是不對的。
可小馳不聽,他只是個孩子,他只想讓爸爸媽媽在一起。
很快,裴延禮發現了,這一招也失去了作用,直到小馳的死訊傳到他耳邊,他都以為是小馳跟他開的玩笑。
在這座房子裡,我遇見了裴延禮,失去了母親,有了孩子,又失去了孩子。
或許是真的走到盡頭了。
這些過往走馬觀花出現在腦海里。
裴延禮是凌晨回來的。
他懷裡擁著一隻通體雪白的小貓,拿著小貓的爪子碰觸我的鼻尖,「小枝,你要的圓圓,我給你找回來了。」
是圓圓嗎?
我快要看不清了。
伸手接貓時頓了下,認出了這隻貓不一樣的瞳孔顏色,耳朵上的顏色是一樣的,大小也差不多,可就是不一樣。
是直覺。
「怎麼了?」裴延禮問我,他讓那隻貓在自己懷裡躺著,自顧自道:「以前小馳小,我總覺得養寵物會傷了他,到時候你又要心疼,所以不答應讓他養。」
我垂下了手,不打算抱貓了。
這不是圓圓,為什麼要找一隻假圓圓騙我,要是小馳知道,一定會怪我。
「裴延禮,這個時候了,你沒必要騙我的。」
在這裡,我等了一輩子。
最後卻連小馳的一隻貓都沒等到。
裴延禮怔了下,「騙你什麼?」
「這不是圓圓?」我太過冷靜,冷靜到篤定,「圓圓呢?」
他真的去找梁平霜要了,細看之下,他面上還有巴掌印,領口有些褶皺了,大概是兩人發生了爭執,回來時很焦急疲憊,但還是拿貓在哄我。
「圓圓墜樓了。」
就在裴延禮打了電話後的半小時里。
梁平霜是兇手,但沒人可以懲戒她。
我又痛又悲,但麻木了,「我要走了。」
「你要去哪兒?」裴延禮讓貓從自己懷裡溜走,空出手來,那樣子像是請求,可他請求我什麼?
「回家。」
全身的力氣被抽空了,我眼前一黑,腿軟倒下,最後嘴巴里還在呢喃著三個字:「找小馳。」
可還沒等我找到他,便在裴延禮眼前暈了過去。
11
好吵。
是誰在敲門,在喊我的名字?
拼盡全力想要保持清醒,可混混沌沌的思緒里只有很淡的吵聲,像是殘缺的片段,像是有男人在吼叫,在砸東西。
家庭醫生的衣領被揪起來。
「她是我的妻子,她病了,為什麼不告訴我?」
我看到了。
那是裴家的家庭醫生,站在他身邊的是一臉漠然的賀儀光,他反問裴延禮,「她是你的妻子,她快死了,你才知道她得胃癌了嗎?」
「裴先生,請你冷靜。」
家庭醫生竭力在維護場面,「兩個月多前,我給你打過一通電話,是您親口說,唐小姐的事情跟你無關。」
原來,他早該知道啊。
我遲緩地呼出一口氣,氧氣面罩壓在我的臉上,呼吸聲像是我的倒計時,每一口氣都是艱難而珍貴的。
裴延禮走過來,在死前,我親眼看到了那麼驕傲的男人在我面前低下頭,他想要去拉我的手,又怕弄疼了我,手抬在空中,遲遲沒有放下,像是一個弄壞了心愛的玩具,竭力想要彌補拼湊,卻不知從何下手的小孩子。
片刻。
他捂住了自己的臉,隱隱約約,我聽見他嗚咽的哭聲在病房響徹。
真吵。
可不可以離我遠點?
可惜我開不了口,罵不了人。
不知過去多久。
賀醫生走了過來,我眼皮動了動,看到他白色的影子站在裴延禮身後,「你這樣會吵到她。」
「滾開。」裴延禮壓著顫音在吼,嗓音是嘶啞乾裂的。
他哭了很久。
哭得我都要煩了,我曾以為我的眼淚最多,沒想到他也會流淚,還是為我。
「人都要死了才知道後悔,當初幹什麼去了,她是你的妻子,這麼多年來,你關心過她嗎?」賀儀光一字一句,如針扎心,「以前你懷疑我們,結了婚你還是懷疑,可你有沒有想過,她就只是想當你的妻子而已。」
「我為唐枝不值。」
「我沒想到她會生病,真的,我沒想到。」
醫院裡到處都是重症病人。
他們吃不下東西,靠著藥丸子度日,咳血是最輕的,掏心抽血的疼是每天都要承受上百遍的,這些裴延禮怎麼會知道?
他只當我是為小馳的死在胡鬧,在小題大做,他以為,我還會回去。
他們在我床邊爭吵,絲毫不在意我是個將死之人。
裴延禮輕輕將我的手掖進被褥里,背對著賀儀光,「你不是醫生嗎?你可以救活小枝嗎?」
「她早就不想活了,誰都救不了了。」
到了這個程度,賀儀光說的是真話。
裴延禮:「你出去。」
屋子安靜了下來。
身體的知覺很虛幻,我的手被抬了起來,貼在裴延禮的臉頰上,他親吻我的掌心,有眼淚在往下落,「為什麼不告訴我你生了病?」
「因為小馳走了,你連病都不治了?」
「那我怎麼辦,你心裡只有那個小孩子,分給過一點位置給我嗎?」裴延禮用我軟趴趴的手打自己的臉,「是我不對,我怎麼可以吃小馳的醋,怎麼會去吃賀儀光的醋?」
「我們才是夫妻。」
「小枝。」
「你醒來打我,你想怎麼罵我打我,我都願意。」
他在喚我的名字,我聽得到。
好想掙脫他的手,只因我看到了小馳在向我招手,他在叫媽媽,他說:「媽媽,這裡好黑,我好害怕。」
想衝過去擁抱他。
裴延禮的手卻死死扯著我。
怎麼這個時候,他還不肯放過我?
12
有針扎進我的皮膚里,疼得我蹙緊了眉頭,腳趾跟著蜷縮了下,骨頭縫裡好似都在疼。
藥物輸進我的身體里,疼痛短暫消失了,生命中的疼卻是藥物無法撫平的。
床頭有人在忙碌。
是醫生,是護士,焦急的吵聲伴在耳畔。
心電圖上的生命體徵很微弱了,在瀕死之際,我好像又看到了小馳,他坐在一片柔軟的草地上,小小的身子趴在草里,一抬頭,那張軟軟的小臉上生著一對酒窩,一笑眉毛彎彎。
他甜甜地叫我媽媽,我想要去抱住他,可耳邊還有人在叫我,叫我的名字。
場景變得扭曲,裴延禮的臉出現在我眼前,他在呼喚我的名字,可我想要跟小馳走,我想說停下吧,就這樣離開,是我最後的夙願。
可他沒有停。
這些天他找來了最好的醫生救我的命,可再好的藥對我都沒用了,我沒有了求生的意志,意識都在跟著夢中的小馳走。
可現實里,裴延禮死死拽著我,不讓我走。
直到心電圖上的有了波動。
是他將我救了回來。
他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,我這條命是他的,要我惜命。
我在醫院躺了一周,這一周里,裴延禮寸步不離守在我身邊。
可我知道,我撐不下去了。
在生命盡頭,我卻看到了我最不想要見到的人。
聖誕前夕。
梁平霜站在我的床邊,我這個樣子,她一定很痛快,她觀賞著我的慘狀,將我的醜陋與病態盡收眼底。
可她卻說,「真是報應。」
接著她又補了句,「是裴延禮的報應,這麼多年他耍我,利用我,讓我對他死心塌地,最後卻告訴我,他從沒愛過我,就連送我的貓都要拿走,憑什麼?」
耳邊的聲音斷斷續續,一句接著一句,砸進我死水一潭的心中。
原來到最後,我們誰都沒有得償所願。
「唐枝,你一定很納悶,為什麼他會恨你的孩子。」
梁平霜低頭覆身,側在我耳邊,在我還有呼吸時,給我致命一擊,「因為他以為,那是你跟賀儀光的孩子,是我告訴他的,是我假造了親子鑑定書,他就信了。」
大笑幾聲。
她身子都在顫,眼角卻擠出淚花,「他真的就信了!」
胸腔里在劇烈跳動著,我已經分不出那究竟是憤怒還是其他了,梁平霜卻還沒停止,「你知道嗎?你的孩子死的時候,裴延禮這個親生父親竟然是慶幸的,他以為這個孩子死了,就能跟你重新開始了!」
他以為的開始,殊不知卻是結束。
撐著沉重的眼皮,我半睜開眸,活動手指,第一眼看到的是從外面走進來的裴延禮,他提著梁平霜的胳膊讓她滾。
梁平霜一聲聲嘶吼著,「裴延禮,你活該,活該!」
他是活該。
我更是。
梁平霜來後裴延禮大發雷霆,他罵了很多人,像是無力的宣洩,他想要喂我喝水,可唯有他喂的我不喝。
只好護士來喂。
他在旁看著,等護士走了,想要替我擦拭嘴角,我側過臉去,看著窗戶外的飄雪,虛無地張了張嘴巴,「快聖誕了吧?」
裴延禮:「是,明天聖誕節,我們一起過節?」
我要熬到那一天,去見我的小馳。
「小枝,我會治好你的。」裴延禮強行握住我的手,他想要撫平上面的針孔,卻做不到,「我早應該知道的,你瘦了那麼多,臉色那麼差,我怎麼沒發現你病了?」
他是沒發現。
可我告訴過他的。
我是說了的。
那天,我問了一句:「最近胃裡總疼,要是絕症可怎麼辦?」
裴延禮聽了只是放下筷子,「那不要死在這裡,太晦氣。」
現在真的是絕症了,他難道不覺得晦氣嗎?
13
聖誕節的夜晚總是熱鬧繁華的。
聖誕樹很漂亮,綠色的,佇立在商場中央,掛著許多裝飾物,路過的行人大多都會停下拍照,彩燈打開閃爍著、將每張笑臉都照亮。
我坐在車裡,裹著厚重的衣物,帽子遮住了眉毛,只留在外一雙眼睛,隔著車窗,望著聖誕的夜晚。
下雪了。
雪花是白的,很純凈,像是小馳的眼睛。
是微笑著的,也是失落的。
那一次也是在這裡,我抱著小馳坐在車裡,他指著那棵聖誕樹說漂亮,我跟他一同看去,看到了樹下站著裴延禮與梁平霜。
他們在那裡合照。
我心一緊,忙捂住了小馳的眼睛。
在茫茫雪霧中,我好像看見了小馳正穿著紅色的毛衣坐在樹下,他摸著聖誕樹上的小鈴鐺,「媽媽,這個好漂亮。」
是很漂亮。
可小馳的笑臉不見了,取而代之的是裴延禮焦急的面色,手臂圈著我的肩膀,讓我靠在他懷裡。
「小枝。」
我好冷,他想要給我溫暖,可他忘記了,自己就是一塊冰,「要不要下去走走?」
我搖頭,只遠遠地瞧上一眼,就當作是替小馳過這個聖誕了。
雪還在下。
力氣在減少。
裴延禮好像感受到了我體溫在下降, 緊接著搓著我的手腕,可上面大片大片的淤青,全是扎針留下,「小枝,你是不是冷?你跟我說句話好不好?」
他臉頰貼著我的額頭,還是那股子清冽乾淨的氣味,卻讓我覺得好遙遠,遠得像是上輩子的事情。
這些年,他留給我的氣味大都是梁平霜身上的香味。
坐在車裡,他跟我一起賞雪, 下巴摩挲著我的頭髮,車廂中很安靜溫暖, 風雪被隔絕在外, 我與他一起看雪。
他的聲音如絮,很輕地飄在我耳邊,「小枝, 你還記得那年我為什麼不解釋我跟你的事情嗎?」
「我應該告訴你的,這麼多年, 我分明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告訴你的。」
雪勢變大了, 小馳在那邊冷不冷?
沒關係。
我很快就要見到小馳了。
畢竟這是小馳的最後一項心愿:永遠跟媽媽在一起。
眼皮上像是凝結了一層霜,我合上眼眸, 原來人在最終失去的是聽覺,靈魂像是脫離了身體, 可裴延禮的話還在繼續,「小枝, 如果不是爸爸告訴我他要娶你媽媽,如果不是他讓我把你當作妹妹,我們不該是這樣的結局。」
「你說是不是?」
「小枝?」
「小枝, 你很冷嗎?」
「小枝,你等等我。」
我不等了他,我要離他遠遠的,下輩子,下下輩子, 都不要再見到這個人。
聲音變得好遠好遠。
好像有哭聲,有人在叫我。
光變得很微弱了。
在我的視線中,擴大、又縮小。
我很累。
眼皮很沉, 抬不起手,想要抱一抱小馳, 捕捉到的卻是一團影子, 我一直追一直追,哭喊著、奔跑著、一直走到盡頭。
大汗淋漓,氣喘吁吁,終於看到了小馳。
他懷裡抱著雪白的圓圓, 「媽媽,你來了?」
這一次,我終於抓住了小馳的手。
(全文完)
 喬峰傳 • 18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18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740次觀看
奚芝厚 • 740次觀看 花伊風 • 1K次觀看
花伊風 • 1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66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66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1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10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83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83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1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1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95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95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77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770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開心果 • 760次觀看
開心果 • 76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1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1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7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700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40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40次觀看 花伊風 • 180次觀看
花伊風 • 18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33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33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41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41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74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74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4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40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32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32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50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500次觀看 幸山輪 • 560次觀看
幸山輪 • 560次觀看 花伊風 • 560次觀看
花伊風 • 560次觀看